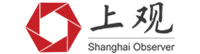阿勒泰的野花
阿勒泰的野花
蒲公英是我们阿勒泰春天开放的第一朵花。在东戈壁上,河滩上,北河森林里,小院里,金色的崭新的蒲公英花像一盏小小的向日葵,更像一枚金色的小太阳,带着几片锯齿般的绿叶精神抖擞地告诉我们,北国大地真正的春阳照射下来啦,大地松动,河水畅流,树木抽出新枝和绿叶。我们俯身轻轻抚摸它,然后站起来,自己也是一个崭新的人。春风荡漾,穿透我们小小的身体。
六七月,蒲公英的艳黄花朵变成了蓬松的白绒球。我们这时候才愿意伸手摘下它,对着旷野吹出一口气,无数蒲公英的孩子去了无边的天地,这就是生生不息的意思了。
蒲公英是我们年少时的好伙伴,我们的乡愁里有它坚固的存在。去年盛夏,我回乌鲁木齐,在南山,母亲采集了一袋蒲公英。母亲用蒲公英和肉馅为我们包饺子,我和姐姐还像幼时那样,静静地等待饺子出锅,然后热切地扑上去,野蔬有韧性,清新回甘,滋味佳。
蒲公英生长在中亚、欧洲、北美洲。在中国,它们的身影主要在华北、西北、东北的土地上。所以蒲公英是我的乡愁之花,就很合理了。《本草纲目》里李时珍称呼蒲公英为孛孛丁、婆婆丁,介绍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中低海拔的田野上。春季开黄色花,风吹飘扬种子,带根带花带叶全草晒干为药,味甘性平,入肝、胃经,有很多功用。清代陈世铎《本草新编》这样说蒲公英:至贱而有大功。
蒲公英有一个很厉害的称号:药草皇后。因它在北方实在太常见太易得,且有一个妙处:有苦泄而不伤正,清热而不伤胃。与其他迅猛如瀑的降火药不同,蒲公英很温和,且于平朴中生发多种疗效,这是慈悲为怀,是普度众生,是母仪天下。
 蒲公英
蒲公英
我的乡愁之花还有野蔷薇,是野泼泼生长在森林里的灌木。布尔津县城北河森林里多野蔷薇,六月开白花、粉花、淡黄花,九月结小小如石榴形状的果子,也被叫作野石榴。薄薄的皮是褐红色的,味道微酸微甜微涩,里面的籽粒并不是石榴的饱满多汁,而是略显干燥且有毛絮的。但我们太喜欢蔷薇花了,五朵花瓣,如绸如绢,矜持含羞,在清晨有露珠滚动。蔷薇的叶子也很好看,小小椭圆的,即使枝子上有密密的刺,我们也会挨近了,观赏着,嗅闻着,有月季的淡淡甜香。蔷薇是灌木,它们挤挤挨挨倚靠着一棵大树生长着攀缘着——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神农本草经》里说,野蔷薇生长在两山之间的高坡土地且有流水的地方。布尔津正是这样的地理形貌。野蔷薇果实里的籽粒叫营实,中医这样分析其药性——营实的性是酸的,酸主收,收敛,它又是温的,温性的药。开的伤口,用蔷薇籽可以收口,同时把脓去掉、把里面的水清掉。听说有的人用蔷薇籽煮汤,煮汤药含在嘴里,用以治疗口舌糜烂。我不记得母亲用蔷薇籽为我们治过口疮,20世纪90年代,我们生了口疮就吃西瓜霜或喷云南白药。人们对原生药草并不重视,动辄选择吃药,这使我想到,人间正在被动或主动地失去很多美,就像蔷薇花影照在我们心灵上的那种美。
野蔷薇果酿酒极好,有一种风土人情的味道。我下一次回故乡,定要采摘一瓶,回到江城入酒,与友话蔷薇。猛虎所嗅的蔷薇,肯定是五朵花瓣的野蔷薇,不是现代人工种植的重瓣蔷薇,那种蔷薇结不出果实。
 蔷薇果
蔷薇果
我的故乡布尔津,为人所熟知的药草还有苍耳、苜蓿、蒺藜、荨麻、艾草等。
布尔津县城人家的牛儿每天清晨在额尔齐斯河老桥头集合,有专门的放牛人带着它们往和布克赛尔方向的草原去。苜蓿正开出直顶天穹的紫色花朵,牛儿们在那里反刍复反刍,卧在小海子边悠然望南山。黄昏前的明亮里,它们排着纵队发出“哒哒哒”的清音,一路回到布尔津城,它们的主人正站在桥头。牛儿们身上沾扯着很多苍耳,需要主人耐心地清理。“牧草之王”苜蓿的花语是希望与幸福。这种多年生草本原产伊朗,汉代经西域传入中原。
我熟悉家乡各种植物的性状。苍耳是一年生草本,纺锤形的果实味辛而苦、归肺经,它能够散风湿、通鼻窍、治耳鸣,属辛温解表药;蒺藜也是一年生草本,它平卧生长、善行善破,可治蛔虫病、失明、浮肿、平肝熄风解郁,《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它在北疆的主要使用方式,是煮水擦洗身体,祛风疹和瘙痒;荨麻则是多年生草本,土耳其人认为荨麻可治百种病症。李时珍说,风疹初起,以荨麻点之,一夜皆失;而纯阳之草,苦、温、热,可通十二经。它能开郁安神、温阳降浊,自古以来被人们认为是地之阳,与天之阳对应称呼,简直有神功。难怪《扁鹊心书》中说,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
药草是大地的语言,教会我们与这个世界温柔相处。
 苜蓿
苜蓿
原标题:《阿勒泰的药草,教会我们与这个世界温柔相处 | 忽兰》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本文作者:忽兰
图片来源:本文图片来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