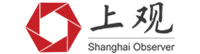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作家阿摩司·奥兹定期与希拉·哈达交谈,希拉·哈达是奥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犹大》的编辑。这些坦诚、不羁的对话展示了奥兹鲜为人知的一面。用奥兹自己的话说,即成为了如今面世的书名《苹果是怎样长成的》。
对话中,奥兹回答了一个作家要面对的那些经典问题,例如是什么让他有了创作一个新故事的渴望,人到中年还如何能去突破自我,此外,小到家庭关系和个人身份,大到尊重不同的文化,奥兹都进行了富有启发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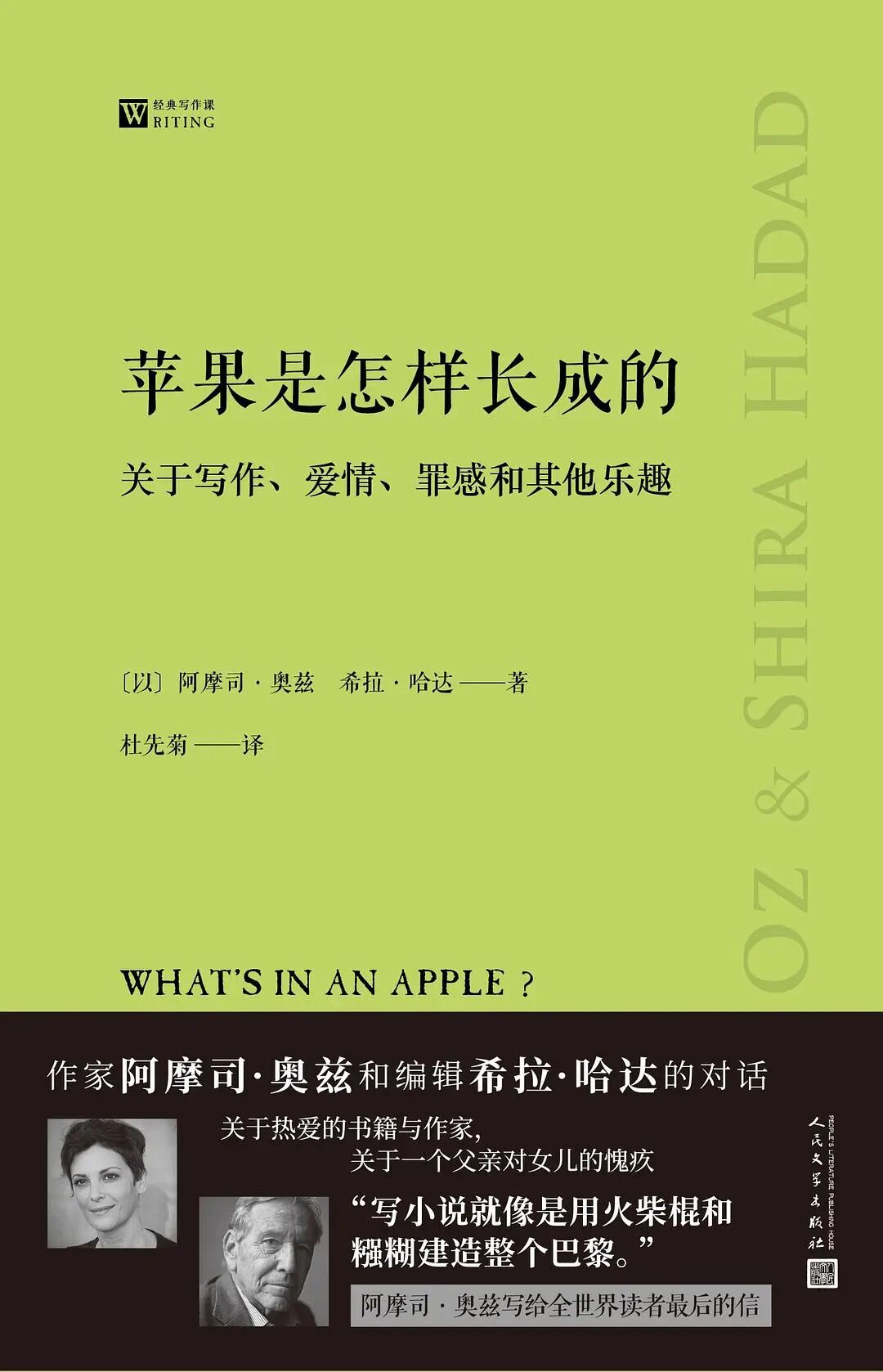
[以]阿摩司·奥兹、[以]希拉·哈达/著
杜先菊/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为一个作家,你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阿摩司·奥兹:在耶路撒冷里哈维亚中学的操场上,有一株桉树,树上有人刻上了一颗被爱情之箭射穿的心。在射穿的心上,在箭头两面,有两个名字,加迪和露丝。我记得,即使是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十三岁,我就想过:刻这颗心的肯定是加迪,不是露丝。他为什么要刻下这颗心?难道他不知道他爱露丝吗?难道露丝不知道他爱她吗?即使那时候,我就自忖:或许,他已经有些知道这一切终将消逝,一切都将消逝,他的爱会有终结。他想留下一些东西。他想在爱情消逝的时候,留下一点关于这段爱情的痕迹。这和讲故事、写小说的冲动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时间和遗忘的魔爪下留存一点东西。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欲望,就是给某种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的东西,提供另一次机会。对,就是这个。我写作的冲动,也来自一种愿望,就是不希望一切被抹掉,不想让它好像压根儿就不曾存在过一样。不一定是在我本人身上发生过的事情。

你觉得你写作的动机这些年间发生了变化吗?还是它们本质上依然是一样的?
阿摩司·奥兹:我不清楚,希拉。我觉得我的动机还是一样的,但我也不特别肯定。我不太问自己写作的动机是什么。当我早上五点钟坐在这里,在空旷的街道上散步之后,手里捧着第一杯咖啡,我从来不问我自己写作的动机是什么。我只是写作。
那你会问自己,这些故事是从哪儿来的吗?
阿摩司·奥兹:会的,会的。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但我并不总是知道答案。我跟你说一点和你的问题有关的事情。我有一次翻译了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一首俄文诗,但我是从斯蒂芬·伯格的英译转译过来的,因为我不懂俄语。这首诗正好说到你问的问题。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我是在一台打字机上把它打出来的。这首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坐在。这里。冰冻的海风
吹过我敞开的窗棂。我不站起,我不
关窗。我让风吹拂过我。冰冻。
黄昏或凌晨,一样蒸腾着的云雾。
一只鸽子轻啄麦粒,从我伸开的掌心
这片空间,没有边缘,我写作的页面的纸张的白色——
一种孤独,模糊的冲动,擎起我的右手,引导着我,
比我更为老到,它翩翩而至,
像眼帘一样碧蓝,不畏神祇,于是,我开始写作。
我不是翻译家,但我想把它从英文翻译过来。说不定这首诗在俄文里更美,我不知道。

我时常也询问自己,这些故事是从哪儿来的,但我实际上并没有答案。不过,一方面,我确实知道,因为我一直过着间谍的生活。《爱与黑暗的故事》里写了。我倾听别人的对话,我观察陌生人,我在医生的办公室,或者火车站,或者机场排队的时候——我从来不读报纸。我不读报纸,而是听听人们在说什么,我把谈话的片段偷窃过来,然后自己把它们补充完整。或者我去观察衣服,或者鞋子——鞋子总是告诉我很多东西。我观察人。我倾听。
......
你懂我的意思吧?这么说吧:我写论文的时候,我写,往往是因为我很愤怒。但我写小说的时候,促使我写作的一个原因是好奇心。无穷无限的好奇心。钻进其他人的衣钵,这种想法令我着迷。我认为,好奇心不仅仅是任何智力作品的根本条件,它还是一种伦理美德。这可能也是文学的道德层面。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亚伯拉罕·耶霍舒亚一直有争议,他把道德问题放在文学创作的前沿:罪与罚。我认为有一种另一层意义上的道德:将你自己放在别人的身份或位置上放几个小时。它有间接的道德份量,尽管这个份量不会很重,我们不要太夸张。但是,我真心认为,一个好奇的人,和一个没有好奇心的人相比,是一个稍微好一些的伙伴,也是一个稍微好一些的人。不要笑,但我认为,一个好奇的人,甚至是一个比没有好奇心的人更好的司机,因为他自己问自己——另外那条道上的家伙能突然干些什么勾当?我认为,一个好奇的人,也是一个比不好奇的人更好的爱人。

你说好奇心是一种人性美德,可以说得通。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好奇心,一种几乎与之矛盾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促使一个孩子撕开一只小鸟,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在你看来,由好奇心写出来、描绘人在其低点的文学,有时会涉及到虐待的,能不能成为伟大的文学?
阿摩司·奥兹:这是对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还有病态的好奇心。我们在孩子身上能够看到,在成人身上能够看到,在作家那里也能看到。那些将一个受伤的人团团围住、观看他受罪、从中得到乐趣的人的好奇心。作家醉心于甚至着迷于恶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或塞利纳的作品,也有一个道德层面。因为他们挑战读者,或者在读者身上激发出道德上的抗体。

你现在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家,人们认出你来。这种“接触现实”的门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是更成问题了?
阿摩司·奥兹:不是。在我观察人的地方,很少有人认出我来。我去餐馆的时候,有时候有人认出我来。如果我在大学里,他们会认出我来。但在汽车店或者在医生那里排队的时候,差不多没有人认出我来。偶尔有人会说,你不是电视上那个人吗?你以前不是在国会里吗?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出租车司机会认出我。但通常情况下,人们不认识我。在国外的时候,当然没人知道我。近些年,我到一个外国城市的时候,我不再去博物馆了,因为我膝盖疼。我也不去看著名景点,因为我看得够多的了。我坐在一家咖啡店的外面,如果天气冷了,我坐在安了玻璃的咖啡店的庭院里。我可以独自坐两三个小时,观察陌生人。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有趣?
你从咖啡馆里或者医生诊所回到你写作的桌子跟前时,你有些习惯性的写作仪式吗?
阿摩司·奥兹:啊,我不会把什么都说出来让你记录下来。如果这儿没有录音机,我可能会多说一点。不是事无巨细。我主要的仪式是让所有的东西各居其位。永远是,让所有的东西都各居其位。这个习惯把我们家人整惨了。有人起来给自己泡一杯咖啡——妮莉,我女儿,我儿子,我孙子外孙,甚至客人——他们离开了一会儿去接个电话,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咖啡被倒进下水池,杯子洗干净了,大头朝下在碗架子里晾着呢。
原标题:《对话阿摩司·奥兹:一个好奇的人,是更好的司机,也是更好的爱人》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郑周明
本文作者:希拉·哈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