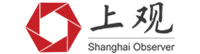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一个人是不应该占尽好处的。或者用我母亲的话讲:有福不可重享。
除了作品,一个作者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多话好讲。一个作者,他的声口就是作品,甚至不应该主动阐释自己的作品。可是,书写完了,最重要的流程开始了:它应该精准地抵达给读者。但现在似乎又少了那么一环。不说话,不发声,作者没有人知道,作品就没有人看到。没人买书,作者以后就很难出书。
无法出书倒也不是不能写。可以写,必须写,可还是会灰心黯淡一些。因为有些作品,是很需要读者的。它渴望一场共鸣。它的作者就是怀着这种想被阅读到,被共鸣到的心情,书写了它们。不能抵达,是很遗憾的。
在大学时,为了凑学费,我做过手机销售员。站在柜台里,端着样机,卖力地吆喝它有多好。我还真是个好销售,充满热情,耐心介绍,制霸暑期销冠。
所以我想,现在我还是要重拾旧业,出来吆喝一番。但卖书跟卖手机还是不一样。那时候手机是一种刚需。现在,阅读未必是刚需,何况阅读里又有那么多门类、那么多“型号”的作品可供选择。
“双11”时,我特意搜了下几个奋斗在写作一线的朋友们的书,看完后,宽慰自己:别害怕,他写得那么好,销量也没有很明朗,你又不是独一个被读者冷落的——可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我们的书写出了问题?就接受读者越来越少的事实吗?我们努力写了,或者把一切推给“时代”,说是“文学式微”了,说作者没生在黄金时代?
这些问题,我还没搞明白。但不妨碍我故作镇定地亮出喉咙,来讲一场创作谈,说说我为什么写,说说我写了什么,一如17年前,我试图去说明手机的主要功能和适用人群,希望百忙之中看到的人会有兴趣翻一翻。
好了,这本书讲的是“罪与罚”和“自我救赎”。《皮影》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影子,面对贫富差距和灵魂的残缺,错愕不及。它来自我对于贫富差距、一个人“表面如何”和“内在如何”错位感的好奇。《二十一日酉时》,题目就是个字谜,谜底为“醋”。醋有一种天然的故事感,它跟酒同宗同源,只是发酵不同,一个成了饮品,一个成了调味品,酿醋的过程就是跟时间较真的过程,这很有意思,我就写了村庄被“换亲”的女孩第一次面对女性的情欲。《山隐》是另一种好奇心发作:想知道,荧屏中光彩夺目的女明星,到底私底下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的家人又因为她的“成功”而过着怎样的生活?所以我让女明星的妹妹顶名而生,大胆地展露出她的嫉妒、难堪和孤独。《食劫》里,写了做鲁菜的讲究和规矩——就像人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里就有了一个女人,她不想要别人给她的“位置”,她想要去创造自己的“位置”,她跟那些古老的规矩就有了一些龃龉。《巡山久不归》中,大山抛出了尸体,巡山的人在找寻罪案真相的过程中,不断映照自身的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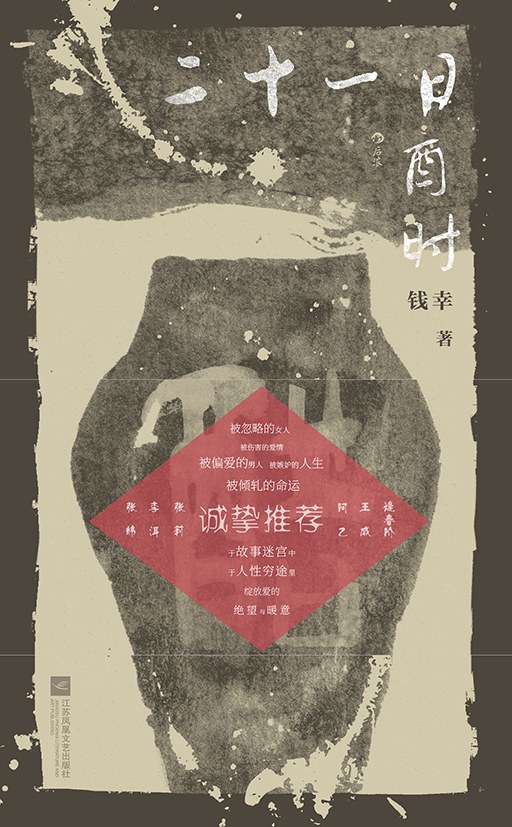
写一篇小说,就像翻越一座山头。攀爬中,会劳累辛酸,但只要坚持,等腿有了机械运动的惯性,那么,痛快和畅然也会从天而降。我就在山脚下,对于这样的爬山,再熟悉不过了。它不是追求“速度与激情”的,正相反,它追求的是“耐力和深情”。现在,这些披着“罪与罚”的故事,都源自我对人的“深情”。我实在是太喜欢研究人内心的疙疙瘩瘩、沟沟壑壑了。而罪案就是这些疙瘩、沟壑的最好的隐藏地。一个人因为有了秘密,脸上有了慌张,心底有了脆弱,而秘密的天性就是要找到出口的,所以窖藏不住,不断往外涌的力量跟不断掩盖的努力相互碰撞,就产生了迷人的裂隙。人性就是从这些裂隙中透出了光和影。
每当在新闻上看到罪案,那个问句就会脱口而出: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不那么做?我问了,但很多时候,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怎么办?我就试着在书写中努力去靠近答案。我对笔下的人物其实挺狠的,把他们逼到了墙角,逼得他们狗急跳墙,现出原形,要他们对命运做出最残酷也最真实的反击。当然,有时候顺从也是一种反击。
写作者挺残忍的,就那么看着他们堕落、崩溃、犯罪、搏击、被侮辱与被戕害,看着他们被生活一遍遍痛打——有时候也会反思自己,为什么总要写痛打、写戕害、写痛苦和卑微?为什么不能写点儿和平静好?为什么不能写平淡顺遂?为什么要写“呜呜呜”,不写“哈哈哈”?没办法,这是写作者的个人趣味和偏见决定的——我想这也是世界的多样性的所在,每个写作者的趣味和偏见都不同,他们会在书写领地上“画地为牢”,做出自己对命运和人的独特理解。
我深深地被那些遭受命运不公的人震撼,所以斗胆想要书写这个领域。为了跟我循规蹈矩的日常界限分明,我创作了这一系列的故事。我的日常很平淡,所以故事都是激烈的。我的日常“两点一线”,所以人物有着大起大落。我一开始是塑造者,写着写着,人物都背叛了我,开始自说自话,有了“小九九”、各自打算盘,激烈地予以反抗。得,他们自由了。这时候,我们就不是写作者和人物的关系,而是互相陪伴的平等主体之间进行一场相互尊重的塑造。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我在塑造他们,他们也反过来塑造了我。
虚构的魅力就在这里,是无中生有,却又“有”得那么逼真。同时,一个写作者的虚构,最终也会组建成这个写作者的精神族谱。虚构反哺着虚构者本身。
仔细想来,书写这些也跟我的经历有关,我是“穷”过来的。“穷”看上去很平淡微小,不足为奇,在穷的个体内心中实际是惊涛骇浪的。我父母进城务工,离开了村庄,又融入不到城市。我们租住的房子,总是漏雨。父母总被生活捶打着,却也在夹缝中勉力生存着,并且尽量撑起身体,为孩子在城市里腾出一些空间。所以在我的想象中,父母的身体总是佝偻着,像是被热辣生活灼痛的虾,而我就是环绕在他们腿部的虾籽。
那时候,我们总感到贫窘,贫窘就像衣服上一小块补丁。别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但我们为了掩盖这个补丁,局促不安,小心谨慎,很容易就觉得害臊——后来想想,奇怪了,为什么反而是贫窘的人要感到不好意思呢?为什么要对不是自己的错误感到害臊呢?没办法。“穷”也是一种游离于人的意志的境遇。因为它,人们早早生发出了敏感的自尊,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来精打细算了。其实,如今想来,正是这些才给了我面对生活的勇气。我现在还是有“穷”的思想,还会有一种“不配得感”。以至于,在写作上稍微摸到一点儿眉目时,还常常感到诚惶诚恐——凭什么是我?
在对自己内心探寻了多次后,我开始释然了。因为这也是我这个人的一部分,这份“穷”也赐予了我很大的“富”。这种“不配得感”会持续带给我危机和鞭策,我大概就是在这种“不配得感”中努力去寻找一种“肯定”。我希望自己佩戴着这份“不配得感”,永远在文学路上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继续追求来自读者的“肯定”。
我写的时候,是认真诚恳的。菜做好了,顾客也可以选择不来吃。可我是个厨子,没有别的本事,我还是要做的。假如你路过了,觉得能夹一筷子,尝尝,不管最终会不会坐下来,起码,能说出它的味道——不好吃也是一种味道。所以,它总是抵达了。是我们共同拥有了我书写而你阅读的这段时间——这场共振的愉悦。
《二十一日酉时》是一场阅读的共谋。现在,我打开了醋坛子,故事便氤氲荡开,直到坛底空明。但新的酿造,已经开始了。
原标题:《钱幸:带着一种“不配得感”,永远在文学路上如履薄冰》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袁欢
本文作者:钱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