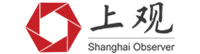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今日去世,享年99岁。
吴孟超1922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治病救人78载,九旬高龄依然坚守在门诊、手术室和病人的病床前。吴孟超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我国肝胆外科开拓者和创始人。
如今,全国肝胆外科的专家和医生中,八成以上都是吴孟超的学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麻醉科主任俞卫锋,亦是吴老的弟子。今年一月,俞卫锋曾写下“‘侧’身吴门三十载,师恩春晖润我心”,这也是他拜吴老为师、跟他学艺的30周年。“这30年与我而言,是思想日趋成熟、精力最为旺盛、经验不断丰富的阶段。”俞卫锋说,在人生这一“辉煌”阶段,有幸成为吴老手术台上的“麻醉专职搭档”,让他没法不自豪与骄傲,他也时常把它称为“最美的相遇”和“一生的荣耀”。

几十年的朝夕相处与默契配合,师徒曾完成了一台台完美的肝胆外科手术,救治了无数濒临死亡的生命。俞卫锋说,也让他近距离切身感受了恩师爱党、爱国、爱民的“三爱”情怀,深深体会了老师勇闯禁区、勇于创新、永不满足、永远争先的“四勇”精神和大医精诚。
在沉痛悼念吴孟超院士之际,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摘编《“侧”身吴门三十载,师恩春晖润我心》一文。

拜师之难
进入大学伊始,我便立志成为吴孟超的学生,这一份崇拜之情至今难忘。在那个年代,解救患者于苦难之中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是每一位医学生心中的偶像。因此,我前半生的医学之路也是追星之路。但我的拜师之路极其曲折,历经12年的不懈努力才让我如愿投到吴老门下,但还是没能让我从事梦寐以求老师所擅长的肝胆外科专业。
我196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一个教师家庭。1980年高考成绩名列全县第七名,填报志愿时在班主任的强烈推荐下,报考了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这一方面满足了从小就有的军人情结,另一方面觉得能做个医生而且还是军医非常不错。这是我主动为自己的人生做出第一次转折——去上海,当军医。
来到大学的第一场入学教育就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创造了肝脏外科界数个第一的吴孟超教授入学讲演。一场讲演听完吴老的奋斗史,年轻气盛的我一阵热血沸腾。也就是那一天,我下定决心要跟随这位老师学本事、做大事。在来到大学之前,他代表了我的家乡人民对健康的向往;来到大学之后,他诠释了我对医学殿堂所有的憧憬。
1992年,我的硕士老师王景阳教授正式退休,而且当时二军大麻醉学还没有博士点。因此,硕士毕业后我迫不及待地报考了吴孟超院士的博士研究生。结果,我考试成绩依然优秀,尤其是专业课肝胆外科学和专业基础免疫学考出了当年所有考生的最高分,照理录取应该无任何障碍了。可是,当年考吴老博士生的考生很多,吴老倾向录取有肝胆外科专业背景的学生,所以我复试就没有通过!眼看多年的努力又要付诸东流,我心情极其沮丧地回了家。家人看到我的样子心疼地说:“是否找吴老的得意弟子杨甲梅教授再想想办法?”当杨教授极力向吴老推荐我时,吴老根本不为所动。眼看我就要陷入绝望。
天无绝人之路。被认为最懂吴老的杨甲梅教授终于找到突破口,他问吴老:“您知道那个俞卫锋是谁吗?他是天天配合您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小俞的老公啊。”大家都知道吴老是出了名的对医生严厉对护士宽容。经常在查房时对护士笑容满面一脸春风,可一转脸对医生就“凶神恶煞”。就这样,我最终还是借着老婆的光非常曲折但如愿投到梦寐以求的吴老门下。
多少成功的背后,就有多少曲折和痛苦。凡事都有因果与安排,你选择了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就会有怎样的回报。成功也在于自己对生活的抉择, 不同的抉择就会有不同的命运,如果我们选择了积极,人生就充满动力和激情。若选择了消极,人生就平凡乏味,没有趣味。我的拜师之路可谓曲折,但我的抉择可谓热诚。
伴师之乐
恩师吴孟超院士在外大家都尊称他为吴院士,而我们学生更愿叫他“老爷子”“吴老”或“校长”。他在当代医学界的江湖地位毋容置疑,想成为他学生的大有人在。所以每年报考他的学生无数,竞争不能说“激烈”,只能说“惨烈”。一般博士生导师58岁就关门了,可我们“老爷子”一再延长招生的年龄。我1992年考他博士时他70整,我当时想兴许能幸运地成为老师的关门弟子。30年后的今天看起来当时想当关门弟子的想法是如此天真,因为直到现在当我即将关门的时候,他招收新学生的门依旧开着。
吴老的学生当然几乎都是肝胆外科的,我是极少数“旁门左道”的学生之一。所谓的“旁门左道”就是非外科医师,如麻醉、病理、影像等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在当年还很落后,自己专业没有博士生导师,只能挂靠外科的名师。所以我们这些少数人的拜师之路就更加的艰难,尤其是像我这样“动机不良”的学生。为什么说我“动机不良”呢?主要是我想通过挂靠途径由“默默无闻”的麻醉医生改行成为“牛逼哄哄”的外科医生。如前所述,我是 “屈打成招”而被成为麻醉医生的,当年我根本就不想做不能被人理解和尊重的麻醉医生,不做衬托红花的绿叶。现在,我终于投到老师门下可开始我的外科之梦了。当我还沉醉在沾沾自喜之中,猛然发现自己完全误判了形势也低估了“老爷子”的“狡猾”,最终我也没逃脱他的“如来佛掌”。
因为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就是要组建世界上第一个肝胆外科医院,当然最缺的就是我们这些“旁门左道”的专业。
其实,早在他当时听从杨教授建议收我为徒时就已为我规划好未来了。也就是说他早就放出了圈套布下了陷阱,等着我自投罗网了。结果就是我比人家付出更多的努力几经曲折成为了外科名师的学生,可是我依然还是一名麻醉医生,所不同的是一个还算很成功的麻醉科医生。
25年最大的快乐就是能配合老师完成一台台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老师每一个举手投足我都能心领神会,即使在外人看来不经意的一个眼神我都能八九不离十地做到无缝对接。几十年没被他老人家训斥过的弟子或下级医生绝无仅有,但我是个例外。这种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的高度默契,发展到最后就成了高度倚重,也为我日后离开部队去地方发展大大增加了难度。
手术室是吴老的战场,也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有人问我吴老到底多喜欢手术室,下面的事例可见端倪。
他每天总是第一个进手术室,先每个房间巡视一遍,发一顿牢骚:怎么年轻医生比我还晚到?逮到一两个不顺眼的外科医生就好好教导一番。开完刀还喜欢“赖”在手术室不走,再每个房间巡查一遍,少不了又是一顿指点江山。然后捧上我和护士长早为他准备好的满满一大杯雀巢咖啡瓶装的茶水,坐下来和我们一通海阔天空讲故事,故事内容几乎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牛奶的故事”这类“陈芝麻烂谷子”过往。所谓“牛奶的故事”就是他年轻时在麻醉科轮转了半年。其间,有一次他做完麻醉后出去喝了一杯牛奶,回到手术房间发现病人心脏已停跳,虽经紧急抢救脱险,但病人预后不好。这次“擅离职守”令他教训深刻。以此教育年轻医生尤其是麻醉医生责任心有多么重要。这个故事我听了不下百次,也和我的学生复述不下百次。还有,他把手术室亲切地称为“开刀房”,把麻醉科称为“麻醉房”。他习惯在开刀房洗澡和方便,即使他办公室在二楼,也要去三楼的麻醉房和开刀房的厕所方便。这种习惯即使在周末节假日甚至年初一也不例外。为此我们开刀房为他专门设置了老年人洗澡方便的安全设施,他见到这些虽然非常简陋但不失温馨的设施也是由衷地高兴。另外,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战士最高的荣耀就是战死在疆场,所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最后倒在手术台旁。关于他的这个想法,很多人颇有微词,认为有点不顾病人的安危。其实我个人的理解这更大程度上是精神层面的,用于表明他恪尽职守献身医学的决心。
还有一个吴老比较著名的故事,他的二女儿因肠癌肝转移入院。很多人劝吴老请其他人完成手术,可吴老坚持要亲自上台。一个90多岁的老外科医生要给60多岁的女儿手术,这是何等煎熬的场面,要有何等坚强的心脏啊!
当天,我们早早在手术室做术前准备等待他们父女的出现。他选择了杨甲梅、沈锋、杨家和教授做他的助手,当然我来主麻。一切就像平时普通手术一样那么按部就班,所不同的就是不像平时手术那样轻松。整个过程是出奇地静,寂静得就像走进了一个无声的世界。平时吴老手术时总要免不了对下级医生指导或训斥,有时还“爱管闲事”地干涉一下麻醉或护理的事。那天我记得从头至尾他没发过声音,只是紧锁双眉,高度专注。打开腹腔后发现病情其实比预想的还严重,特别是肝脏的转移灶多得几乎数不清。作为一个经历无数大小手术的医生,处理很多复杂病情都得心应手,可面对自己女儿的严重病情又是那么无奈。我们看到这样的场面也是心情相当沉重,很想安慰这个悲伤的老父亲,但确实找不出合适的言语。只能和他一起默默分担并尽一切可能把手头工作做得完美。
他虽然长期专做肝胆手术,已多年不做肠道手术了,可他还坚持亲自为女儿切除肠道肿瘤。还不用现代常用的吻合器进行缝合,而采取最经典的传统手工缝合方式一针一线层层缝合。他是那么相信他双手的过硬技术,他要亲自用自己的双手缝合他女儿身体上的伤口,以抚平他自己心理上的巨大创伤与痛苦。面对肝脏上众多的转移灶,大的一个个切除,小的用微波针一个个烧灼。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不可能彻底根除,即使可见到的瘤子全部处理掉,还有无数看不见的肿瘤细胞未来还会生出瘤子。但这位执着的老父亲非常耐心地一个一个瘤子加以处理,生怕留下一个种子放跑一个敌人。
经过了几个小时生理心理的双重挤压,看着老师略显佝偻的背影和踉跄的步伐渐渐向外走去,我们都非常伤感和心痛,那一瞬老师仿佛又苍老了许多。那晚,他给我们上了一场非常深刻生动的人文教育课,让你一辈子体会不完到底如何为人父如何为人师?正如他常教育我们的:“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陪伴老师的每一天都值得细细咀嚼,配合老师的每一台手术均是精彩过往。只能留作以后写回忆录时一一道来、慢慢品味了。
离师之痛
看过太多的分手场面,终于轮到我做主角了。
从1992至2017在老师身边工作整整25年,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5年。虽然我不是在吴老身边坚守最长的学生,但绝对是最忠诚的学生之一。25年中面对过许多外界外院抛来的橄榄枝,或是因为担心我的离开会影响老师的事业,或是因为在老师呵护下总感到那么安全与踏实,结果都被我一次次放弃了。直至2014年底我51岁,我决定抓住也许是人生最后一次闯荡拼搏的机会,加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应聘担任该院历史上第五任麻醉科主任。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对肝胆外科医生来说绝对是个好平台、大平台,但对麻醉学科来说确实太过局限,操持一些大计划、大项目、大成果难度太大。人家可能稍作努力就能获得的东西,我们就要付出超常的拼搏才能获得。所以我时常觉得无法做到指哪儿打哪儿的状态,一直渴望能得到一个更大的平台来展现我的毕生所学。25年中这样的机会不少,但就是觉得还有很多的事放不下,有太多的留恋与不舍。年过50后看到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应该是时候做出决断了,同时我也觉得时机也基本成熟了。
虽然有了要离开的想法,并自认为也考虑成熟了,但最终还得过老师这一关。
我怯生生地找到老师和盘托出我的想法,老师顿时拉长了脸,生气地说:“为什么要走?我对你不好吗?”对这样的结果我事先早有预料,如果他爽快地马上同意我走才觉得意外或失落呢。于是,我提出那能否去仁济医院兼职麻醉科主任呢?当然这也是我从仁济医院李院长那里争取来的三年可兼职的优惠条件。我对吴老说:“同时兼职两家医院,使我们规模较小的专科医院麻醉科可依托仁济综合医院的大平台,实现在后备人才培养、医疗资源共享等多方面双赢的局面”。此时,正好肝胆医院新建规模很大的安亭新院区,并探索大专科小综合的新路子,这一方案正好说到老师心坎上了。老师将信将疑半推半就地同意接受跟仁济医院分享一个麻醉科主任的折中方案。这个听起来两全其美的方案实现了我曲线救国的目的。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军地两用人才”,从而开创了骑跨军地两界,管理一所综合一所专科三甲医院共8个院区麻醉科的国内先例。
三年时间转眼即逝,兼职的最后期限很快到了。2017年,第二军医大学又转隶海军成为海军军医大学。所以这种骑跨军地的方式显然是行不通了,也到了该真正离开的时候了。当然,这个时机相比于三年前也更加成熟了。所谓的时机成熟,一是此时老师已95岁高龄,不再像以前那么多进手术室开刀,对我的依赖性大大下降。也实现了我当时对老师的郑重承诺,就是一直陪伴他开刀直到他不开为止。这样也才使我那不安的心找到踏实的安放之处。
老师看到我在地方发展很好,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毕竟,谁都希望自己的学生有出息。深明大义的老师也看到地方更大的舞台更适合我,所以于2017年7月1日正式为我签署了放行的命令,为我37年的军旅生涯画上休止符。脱下习惯的军装,在老师骄傲的目送中,我继续前行,为中国麻醉学科去做更多的付出。
龚自珍说过:“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故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来到外面的世界里将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开放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互为映衬,正是我离别军营时的内心真实写照。诗的后两句则是老师的内心写照,陪伴老师是学生的孝义之情,去到更大的平台为中国医学事业持续付出,是一名成熟的学生对老师这位伟大医者最大的报答之义。
说实话,离别还是很忧伤的,师生情谊就像两个人相爱是甜蜜的,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少幸福的笑声,分开的时候就有多少绝望的泪水,所以说即便你再爱他,也未必能够长久留住他的情。分别虽有撕心裂肺的痛,但人生苦短,大可不必苦苦纠缠折磨自己不放。即使你对曾经的美好念念不忘,但总归要做到该放就放。正如汪国真所说:“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请不要留恋身后的山水,也不要沉醉于当下的田园。背起行囊,剑指远方吧。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远方才会有广阔的天地。它容得下你的壮志,也安放得了你那不羁的心。唯有在广阔天地里创造出辉煌的成绩,才能真正回馈老师的精心培养和大度理解!
栏目主编:顾泳
本文作者:黄杨子
文字编辑:顾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