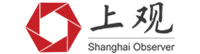今年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余源培先生的本命年。
一辈子学习哲学、研究哲学,余源培始终保持一颗热诚之心,也以个人经历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新中国的前进与发展。
耄耋之年,他一方面深感自己的局限,一方面坚信新时代是大有可为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相信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一定会做得更好”。
我名字里的“源”字取自湖南桃源
上观新闻:您是江苏人,却在湖南出生,后来又去了四川,时局的动荡早早地就在您身上留下了印记。
余源培:是的,我是在抗日战争的风云中出生与度过幼年时光的。1938年4月,我出生于湖南桃源,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二。我名字里的“源”字,就取自这里。
我的父亲余俊生,一生献身于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在四川大学、安徽师范学院等高校任职;我的母亲张淑宜节俭持家,心地善良。父母一生为教育子女成长,含辛茹苦。如今我人到老年,倍增对父母养育的感恩和对生命坎坷的敬畏。
抗战时期,我们一家人和全国亿万同胞一样历经劫难,还在重庆大轰炸中死里逃生。1945年,我尚年幼,国人欢庆抗战胜利的热烈场景仍然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决定回到江苏泰兴,与祖辈团聚。因此,我的小学教育是在苏北农村完成的。1949年前的苏北农村生活十分艰苦。我享受到了田野的乐趣,对农村的自然性、本根性有一些接触,也经历了贫穷、落后生活的磨炼,萌生了发愤读书以“跳出农门”的想法。
上观新闻:读中学的时候,您是不是已经算“进城”了?
余源培:是的,我跟随父亲工作变动来到安徽,在芜湖第一中学读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创建于清乾隆三十年的中江书院。在此工作、学习过的名人,有严复、陈独秀、恽代英、蒋光慈等等。
和当时的很多进步学校一样,芜湖一中重视人文培养教化。沐浴在“励学、远志、修身、笃行”的校风下,我接触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感到书中讲的道理十分生动。此外,我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发现了苏联学者尤金和罗森塔尔合著的《简明哲学辞典》,由此产生了对哲学思辨性的兴趣。
上观新闻:您的父亲也是老师,还记得他是怎样教您的吗?
余源培:父亲为人严肃,勤恳认真,有着严谨的科学精神,将教育当作一生的事业、救国的事业。他对子女是比较宽容的,但有件小事对我影响颇深:中学时期,我疯玩了好一阵。父亲虽然没有责言批评,却在我书桌玻璃板下压了张纸条,上面写着“玩耍的时候好好玩耍,学习的时候好好学习”。当时看到这张纸条,我的心智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激励起主动学习的自觉性。
上观新闻:后来,作为老师,您又是如何教育学生的,有什么经验之谈吗?
余源培:青年人有不成熟的一面,在成长过程中也有可能试错、犯错,因而尤其需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要理解、包容、鼓励和引导他们,允许他们有更多的自主发展可能性。我也常常勉励大家保持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遇到一时挫折和困难不要消沉,不要半途而废。我自己一辈子教书育人,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青年人的顺利成长。
比如俞吾金,他刚进哲学系学习时,花了很多精力阅读世界名著。我作为班主任,和他们相处更像是朋友。一天晚上,俞吾金向我倾诉对文学的热爱。我对他说,对文学感兴趣是好事情,因为哲学和文学是相通的。传世的经典文学作品,往往都有它的哲学内核和内涵。我的导师胡曲园先生早期就对德国文学很感兴趣,这对他研究哲学很有帮助。俞吾金后来说我是他转向哲学的一个“引路人”。每每追忆这段月光下的谈心,我都对他的英年早逝倍感痛惜。
“哲学发展意味着人的思想解放”
上观新闻:您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第一届学生?
余源培:我是1956年考上复旦大学的,以第一志愿被哲学系录取。
那年初,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接着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的八大也在这年9月召开,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在这种生机勃勃的形势下,复旦大学哲学系应运创立。经过5年学习,我成为第一届毕业生。可能因为我学习比较努力,又表现出一定的思辨能力,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可以说,历史给了我一个从事哲学工作的宝贵机遇。
上观新闻:建系之初的复旦哲学系是什么样的?
余源培:记得建系之初,学校请来三位苏联专家,分别担任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的讲课。哲学方面的专家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柯西切夫,他还担任复旦大学校长顾问,同时是哲学系建系顾问,介绍和提供了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这位专家的讲课,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第一,比较注重搞清原理;第二,联系哲学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事例较多。
可以说,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办学风格,一开始明显受到苏联的影响。与之相对应,胡曲园先生则注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内容,编写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讲义。他给我们上课,联系的多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革命的事情,听来感到亲切,入耳入脑,印象深刻。
上观新闻:胡曲园先生是您的研究生导师,他是一位怎样的学者?
余源培:胡曲园先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一届系主任。他学识渊博,在哲学的各个领域都有精深研究,却毅然将重心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传播上。他认为,哲学不能只是工具性知识的传授,而要帮助人们解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哲学发展意味着人的思想解放”。
1924年,胡曲园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在听到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特别是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后,为了探求中国向何处去的真理,他决心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是时代重大问题引导他完成了这一转向。

2021年6月,陈望道雕塑亮相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这尊雕塑还原了陈望道在工人夜校宣讲马克思主义时的情景,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设计创作。新华社发
胡曲园先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观察问题眼光十分敏锐,常常走在时代的前沿。1957年,他在《学术月刊》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的一些哲学家“对于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一原理,只从对立的方面加以观察,而没有从统一或同一的方面去了解”,而一旦忽视对立面的统一,“那就有可能,在现实的斗争中,把认识上的矛盾(差异)扩大为阶级的对立,进而把阶级对立扩大成为政治阴谋”。
这一分析,可谓深得辩证法的精髓,在历史转折时期发出了哲学家的睿智声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可以概括成“三句话”
上观新闻:除教学工作之外,您还长期担任《辞海》编委、分科主编。您当初是如何与《辞海》结缘的?
余源培:1959年,经党中央同意,上海组织对1936年出版的《辞海》进行修订。那时,复旦大学正轰轰烈烈搞教育革命,鼓励“学生上讲台、教授下讲台”,便顺势将《辞海》条目先行层层分解下去,让我们学生先弄。然后,老师们不厌其烦地传授知识、提供资料,对写出的稿子提出修改意见。
1964年,包括哲学卷在内的《辞海》(未定稿)得以内部发行。之后,《辞海》进行大修订,听取工人、农民代表等各方面的意见,我也参与其中。1959年到1979年参加《辞海》编写的这段经历,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能近距离接受上海哲学界一流专家的指导,包括冯契、周抗、周原冰、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等。
《辞海》每10年修订一次,我一直担任编委和分科主编,具体负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词条。作为分科主编,我要全面审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全部词条。如果不合格,要么与作者联系,要么自己动手改写,每一条都要签字。在这一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了“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并且不断得以更新知识,为自己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上观新闻: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进入中学、大学课堂。这门“必修课”应该怎么学?
余源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多次参加上海思想理论界的“双月座谈会”。有一次,座谈会的主题是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问题。我在会上是这样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主义真”——确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品德正”——塑造良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道德;“方法对”——培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这三句话,是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切身感悟。
“主义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功能。20世纪的一个重要历史主题就是社会主义问题,关于其中的实践和理论,包括苏联的兴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很多人在反思、在前瞻。解决“主义真”,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上的“应然”变成实践中的“实然”,是非常艰难复杂的过程。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但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恰恰说明,科学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创新发展。
“品德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伦理功能。哲学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哲学家是为人生而研究哲学的,把人生的意义和美德当作主要的哲学问题,如苏格拉底和康德。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就写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中,一直倡导“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生观真谛。
“方法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功能。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也是方法论、认识论。列宁出色地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留下不少著作,如《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列宁的这一做法,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
有些人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误解,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包罗万象的终极真理,一切现实问题都能从中得到现成答案。其实,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不能抽象地谈世情,也不能封闭地讲国情
上观新闻:伴随改革开放拉开大幕,哲学研究是不是也迎来了“春天”?
余源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带动下,哲学界愈发明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不能用孤立、片面、凝固的观点理解,而必须加以联系、全面、动态地把握。在学科建设上,要努力做到如实反映历史的真相、澄清对历史的曲解。为此,必须掌握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而不能仅仅罗列历史事例或者任意抓住个别事例。
1982年初,我在《复旦学报》发表《真理标准研究中应当重视的两个理论问题》,提出人们认识真理、把握真理、运用真理、发展真理,不能囫囵吞枣,不能思想僵化,都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确定具体真理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在实践的基础上,真理的形成和真理的检验应当是统一的,不能用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真理。
上观新闻:为何要强调“掌握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资料”?
余源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入门需正,取法要高”,从事研究更不能脱离对原著的钻研。这是最好的根本途径。学习原著不仅能够直接掌握原汁原味的原理,而且能够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第二手”的各种材料,虽然读起来容易懂,但就其准确性、精华性、科学性来说,是无法与原著相比拟的,其中难免有片面性甚至错误。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曾认为,马克思缺少哲学著作,有的是经济学或历史学著作。旧传统将哲学与经济学分离开来,所以他们要用新康德主义来填补马克思的哲学空白。其实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存在于“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物质生活中”。马克思是从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中走向历史深处,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他把经济学看成哲学联系现实最佳的、最直接的途径,《资本论》就是这种双向批判和建构的结晶。

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发行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蒋迪雯摄
上观新闻: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您有哪些体会?
余源培: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举毛泽东的治学主张为例。
毛泽东早年选择的为学之道,是“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列出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目,包括“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指出“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但同时,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的黑暗与愚昧面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希望国人中“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出现,“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为此,他花精力来学习西方文化,“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比如,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写下了1.2万字的批语,糅合进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用以思考人生和宇宙问题。
当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态度更加趋向革命性和科学性。《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他在马哲与中哲相互激发之下的思想结晶。
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果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产生“水土不服”,就会失去生命力,就会出现教条化。在历史紧要关头,我们既不能离开“国情”抽象地谈“世情”,也不能脱离“世情”封闭地讲“国情”。认识“国情”是为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认识“世情”是为了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怀疑是为了追求真理、热爱真理、献身真理
上观新闻:今年是统一战线政策明确提出100周年。您曾获“上海市统一战线优秀个人”嘉奖,背后有哪些故事?
余源培:1990年,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很快成为区政协委员,随后被推荐进入市政协。在人民政协的舞台上,我抱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志,努力发挥专长,积极参政议政,力争做到讲真话、做诤友。
在市政协八届一次的小组讨论会上,大家纷纷围绕浦东开发与经济发展提出建议。我虽是新委员,但也大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即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即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要以经济为基础,经济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的健康发展。
有段时间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政协委员就是各方面的“知名人士”。我一开始也未能免俗,后来逐步修正认识,认识到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更应当提高自己的“知民度”和“知情度”,要关注民生、关注社会。
一天晚上,我看完歌剧走出大剧院,演出确实很精彩,但票价也确实很“高档”。怎样让广大市民也能享受到“文化大餐”?我受到触动,写了一份《舞台艺术呼唤“平民意识”》的提案,后来以《“文化大餐”应当名副其实》为题进行发表,《人民日报》随后加以转载并配了漫画。
上观新闻:一面翱翔于哲学殿堂中,一面贴近鲜活的现实世界,在这过程中,您有什么心得?
余源培:胡曲园先生晚年曾用张居正的名句鼓励学生:“心以积疑而起悟,学以渐博而相通”。这是他一生追求真理、献身哲学、勤于思考、求真求是的生动写照,也是我研究、宣传、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深切体会。
“心以积疑而起悟”,说的是做学问要有怀疑精神。怀疑是为了追求真理、热爱真理、献身真理,而不是主张怀疑一切。问题如同一块强磁场,能够将人的注意力凝聚而不至于分散,能够积极调动思考和悟性。哲学需要怀疑和独立思考精神,在此基础上渗入自己的主体感受,给出具有新意的视野。哲学思维不仅是求同思维,而且要有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
“学以渐博而相通”,特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精深,不断与人类文明和社会实践与时俱进,不断由时代实践赋予其活力。新时代,要掌握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一定要理论联系实践,更好地推进马哲、中哲、西哲的对话。
今年是虎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我一辈子从事哲学工作,深感知识结构和思想视野都有局限,既有时代的局限,也有个人层面的局限。新时代是大有可为的时代。我相信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一定会做得更好。

余源培 1938年出生,复旦大学教授,任《辞海》编委、分科主编和《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常务副主编,多次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优秀论文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栏目主编:龚丹韵
本文作者:夏斌
题图来源:朱瓅 摄影
图片编辑:朱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