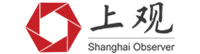落基山在科罗拉多。约翰·丹佛的《高高的落基山》唱的就是落基山多高多远。落基山脉除了海拔高,还以秋色著名。尤其是白杨树成片变色的时候,黄色如海,风吹过麦浪在高山上。
白杨树漫山遍野,在山石之间或低矮植被的空隙地带。树林浩荡,黄色叶片顶峰的集中地愈加耀眼夺目,仿佛大地举着巨大的黄色花束向你扑面而来。黄绿相间的,点点黄色,那是轻盈的小精灵在向你招手微笑。
手机搭在车窗上,对着山岚敞开镜头,风中有片树做的云,便在你眼前展现开来。如若配上约翰·丹佛“落基山脉高又高”的歌声,便有身在旷野如沐春风之欢悦洋溢。
今次所去之地叫鸡冠山。山名有趣,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附近也有个地方叫鸡冠山。
去鸡冠山赶集好像是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有点儿像如今的人去踏青赶海。六七岁的我跟着我爸去鸡冠山,要坐火车,去到一个小镇。那是一个周日的晌午,晴朗的天空挂没挂着白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向遥远的空间瞭望。那是一个开阔地带,像电影里那种集合地,赶集的人不多,最后我们买了一只大公鸡。回到家,我妈迎上来,看到大公鸡半是抱怨半是欣喜。大公鸡身上漂亮的羽毛配上厚重的古钱,就可以做成响当当的鸡毛毽。红黑相间闪光发亮的公鸡羽毛,踢起来就像成熟的麦穗那样弯下腰来,一闪一晃,恰、恰,还带着大钱的响声。色彩鲜艳的鸡毛毽和闪光纸一样,映射出童年的阳光普照。
说回到科罗拉多的鸡冠山,它跟公鸡没关系,大约是横看成岭侧成鸡冠,是故名鸡冠山。也跟集市无关,却以野花著称,夏季的山谷里都是成片的各色野花,摇曳生姿,令人震撼。这里每年夏天的野花节很有名,会令人误以为到了瑞士的山野仙踪。
回到前边提到的约翰·丹佛。他原名henry john deutschendorf jr,约翰·丹佛是后来的名字,因为他住在丹佛。他父亲是军人,总是搬家,父亲又特别严厉,无法示爱。他算是童年的伤痛要用一辈子来治愈的例子吧。第一任妻子是安妮,两个人的婚礼在科罗拉多的阿斯彭举行,金色的白杨树丛林配着白色的婚纱,美轮美奂,婚礼轰动歌坛。约翰·丹佛还给她写过一首歌,名字就叫《安妮之歌》,一蹴而就十分钟写成:
你让我灵感泉涌
如静夜的森林
春天的山岚
小雨中的散步
沙漠中的风暴
沉睡的蓝色海洋
如此琴瑟和鸣,乃至安妮生不出孩子,两人还特别收养了一儿一女。但是后来还是分手,因为丹佛事业成功,总是游走四方演出,聚少离多。丹佛之后的第二任妻子年轻漂亮,两人生有一女,但是也以离婚告终。两任妻子都离他而去,为此丹佛痛苦至极,开着买来的飞机到处游走。这架飞机竟然是一个飞行爱好者自制的,结果打不开某个机关,1997年10月12日,约翰·丹佛的飞机在洛杉矶附近海滩失事,令人遗憾。
最早听到他的歌,是《阳光照在我肩上》。
科罗拉多温差大,早上出来很冷,但是太阳一出来,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很舒服。“阳光照在我的肩上,让我快乐”,他的声音中性,有些微卡朋特的痕迹,歌里总带有一丝感伤:
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让我快乐
阳光照在水上
多么可爱
他还跟多丽丝·戴合作过,就是那个唱“qué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的。
第一次唱《阳光照在我肩上》这首歌时,还是在大二的精读课上。老师刚从英国回来,西装领带,衬衫雪白,眼镜闪闪。还记得他讲狄更斯的《双城记》,同桌闺蜜摆弄手指,不知怎么弄出血,旁边的胖子男生大声道:“血疑。”
“阳光照在我的肩上”在教室里飘荡,“阳光照在水上,多么可爱”,阳光和着记忆,总是如此令人欢喜。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伍斌
本文作者:张欣
题图来源:本文作者拍摄的落基山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