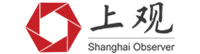10年,9年,75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把94岁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1930年到1940年,是生命最初的10年;1940年,他在父亲吕惠生影响下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一名文艺兵,直到1949年脱下军装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9年军旅生涯画上句点;此后,他为电影作曲事业奋斗长达75年,至今没有停下创作的步伐。
对吕其明来说,上海曾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词。1949年5月26日,青年吕其明在背包上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随华东军区文工团第一次步入上海街市,从此与这里结缘七十载。
“从一名19岁的文艺兵,到现在已过鲐背之年的电影作曲家,是上海养育了我,上海的党组织培养了我,我喝着黄浦江的水,内心充满了对党和上海人民无限的感激之情。”在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了吕其明。他说,这是自己最想说的话。
以下是他的口述。
 20世纪40年代吕其明在华东军区文工团时的留影(资料照片)
20世纪40年代吕其明在华东军区文工团时的留影(资料照片)
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相继结束后,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跟随陈毅司令员顺利渡江。接着,我们来到江苏丹阳,为进入上海做最后准备。
当时陈老总做了一场入城纪律报告。他讲了很多,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要严守“铁的纪律”等,并对上海的情况作了介绍和分析。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陈老总讲的“上海是一个大染缸,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乐园”。他提到上海有一个公园,公园门口有这么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能入内”。听完后,我们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上海对于全国的重要性,同时看到了解放上海的艰巨性。为什么说艰巨?陈老总讲,部队不能开炮,不能炸毁上海的建筑文物,要在“瓷器店里捉老鼠”。最终,上海战役胜利结束,7000多位指战员为解放上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5年前,在庆祝上海解放50周年的时候,上海交响乐团陈光宪团长和陈燮阳指挥邀约我写一部交响乐。当时我反复思考,最想讴歌的还是解放上海时牺牲的烈士们。这些烈士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上海的新生,有的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我们活着的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绝对不能忘记他们。所以我写出了《龙华祭》,希望以此纪念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7000多位指战员。

再说回我们进上海的经过。1949年5月26日,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随部队进入上海。那时战斗到了尾声,上海很多地方已经被解放了。部队坚持不扰民,不入宅;辎重、伙房不入市区,不受馈赠,这才出现了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的场景。我们文工团员没有露宿街头,在老北站的大厅里睡了一夜。那时候条件艰苦,老北站没有椅子凳子,我们就在一条条板条拼接起来的条凳上过了一宿。
第二天,上海宣布解放。我们早晨从北站出发,穿着布鞋、背着背包,精神焕发、整整齐齐地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那时华东军区文工团有6把小提琴,我的背包上就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我们这个团还有一个电影队、一个军乐队,所以还有大喇叭这类乐器。上海市民看到我们这群年轻的男男女女以及各种乐器,都感到非常惊奇。我们打量着这座城市,也觉得很新奇。
我们从北站一直走到位于陕西北路的驻地,那是一个被没收的特务机关,然后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当时文工团的职责是演出,我们在闸北的一个剧场演了好几场,我主要就是拉小提琴伴奏。
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会的成员。很快,军管会要求我们到工厂去做群众工作。我曾经到过两个厂,一个是上钢一厂,另一个是国棉十九厂。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因为当时国民党破坏得厉害,很多工厂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分散到各个工厂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1982年,吕其明凭电影《城南旧事》配乐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资料照片)
1982年,吕其明凭电影《城南旧事》配乐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资料照片)
不久后,我的人生又迎来一个转折点。当时华东军区文工团分为一团和二团。1949年11月,领导作出决定,派二团继续南下到福建工作。我属于一团,就这样留在了上海。同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很多私营电影厂,这些人后来都流散到社会上,所以领导决定要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大量地吸收演员和技术人员。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一团也在这时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作为政治骨干参与电影工作。
那时候,我被分配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脱下心爱的军装,心情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我内心很舍不得离开部队。部队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我在部队成长,是部队培养了我,使我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艺术熏陶,给我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
另一方面,我又感觉到上影厂是一个新的天地。我们在文工团的时候好比是小米加步枪,但是电影厂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大企业,是一个现代化的生产系统。我当时有种兴奋感和恐惧感交织的心理,新鲜之余,觉得自己对电影一窍不通,对于今后的工作很没底。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很多文工团员都有同感。文工团里有演员,有搞美术的、搞电影放映的,有搞音乐的、搞表演的,到了电影厂以后就分到了各个部门。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开展新的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严峻的考验。
1951年,我被调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作曲。面对一个交响乐队,这更是从未有过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提高业务能力。后来,我写《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写《红旗颂》,都是因压力而更加迫切要求提高自己的能力。同时,我也认识到,越是来源于真实生活、越是根植于民族土壤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

一晃75年过去了。这75年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上海度过。回想起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整座城市被国民党严重毁坏,百废待兴。而如今,上海已经成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我是这一巨大奇迹的见证者、亲历者。从个人角度来说,从一名19岁的文艺兵,到现在已过鲐背之年的电影作曲家,是上海养育了我,上海的党组织培养了我,我喝着黄浦江的水,内心充满了对党和上海人民无限的感激之情。这是在纪念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我最想说的话。
(本文为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推出“上海解放口述史”栏目系列文章)
栏目主编:张骏
本文作者:周程祎 顾杰
题图来源:顾杰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