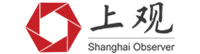上海最炎热的季节,73岁的金士杰在排演话剧。一个半月的排练后,他与田水主演的《父亲》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7月27日至8月11日连演14场,8月15日至18日将登陆国家大剧院。
“每场《父亲》,我们只演给五百多个观众看,演戏、看戏是多么奢侈的事。”金士杰对表演保持着少年般的好奇与进取,他为台词彻夜难眠,看纪录片揣摩角色。
在按部就班的日常中,金士杰时时寻找新鲜的内容。三伏天炙热的阳光洒在安福路的树叶上,正在接受采访的他瞥向窗外:“多漂亮的天光!”
我像站在悬崖边上
《父亲》讲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安德烈不断陷入记忆与现实交错的时空旋涡。他开始无法辨认身处的现实,不理解女儿安娜为什么要坚持给他找护工,更不明白为什么最近一直有陌生人闯入自己的生活。
混乱的思维让安德烈的台词变得颠三倒四。“记台词困难,在我以前排的舞台剧中几乎不存在。”舞台之外,金士杰也在面对挑战,今年初,他的声带做了手术。在上海,他永不离身的斜挎包里装着保护嗓子的中药,他也自觉远离所有饮料与零食。
上观新闻:2014年,话剧《父亲》荣获法国莫里哀戏剧奖最佳剧本奖,先后在超过45个国家上演。根据剧本改编的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斩获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您在接演这部话剧前研究过电影吗?
金士杰:2020年,我在一个小小的手机上看过这部电影。我很喜欢它,但没有完全记得细节,只约略知道大概情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邀请我演《父亲》,差不多同时,台北也有团队找我演类似题材。我被上话的诚意感动,来挑战这一次的任务。
《父亲》讲“迷路”的老先生安德烈,写作方式很奇怪,编剧仿佛直接切入病人安德烈的脑袋里,从他的视角看世界。我演一个神经病患者,我真的要成为神经病患者?各种观念在脑海里翻来倒去,我也有点“迷路”。
我敢演石头,演狮子,演猴子,但演安德烈这么奇怪又与我长得很像的人,我很迷惘。真是这样走吗?走下去会怎样?好几次,我像站在悬崖边上,再走一步就走不下去了。成为安德烈的过程中,我有过不安,又不愿意对不起剧本,我愿意陪着安德烈一起站在雾中摸索、吃苦。
上观新闻:排演《父亲》时,您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
金士杰:编剧弗洛里安·泽勒用了特殊的写作技法,文本像跳帧一样,有时省掉几句话,有时掐头掐尾,有时词语和句式变形,制造出失忆的人脑中的时空错乱。无论谁演安德烈,应该都很害怕,角色在清楚与糊涂之间频繁切换,台词量巨大。一般剧本的台词有逻辑可循,《父亲》的逻辑完全被打乱,每段内容看上去差不多,光背词就把我卡到了,怎么也背不下来。
我手上有至少三个《父亲》译本。由于国情、文化不同,只要是翻译,就会有理解障碍,全世界都一样。有些句子,演员知道意思,怎么传达给观众?编剧写出来的每个字、每个句子都呕心沥血,我当然不遗余力去揣摩那些句子,寻找适当的字词以及表现方式,追求自然真实的表达,让观众看到人物之间的关系,看到编剧想表达的主题。
 金士杰在《父亲》
金士杰在《父亲》
 金士杰在《父亲》
金士杰在《父亲》
上观新闻:您演过形形色色的角色,《父亲》中的安德烈是最难的一个吗?
金士杰:最难?可能不算,我不会想“最”这种问题。
我接舞台剧很小心,几乎不去台北之外的地方排练。接到《父亲》的邀请,答应演出,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在上海一待就是两个月,日夜排练演出,简单说,我被这个剧本打动了。
我刚开始接触《父亲》时信心满满,觉得这个戏大有可为,但后来声带问题让我着急,健康的声带很重要,它甚至影响到我背台词的效率。台词一旦卡壳、犹豫,再怎么补救,也会让演员深感受挫。
我很早就开始与剧本“打仗”,因为必须先做功课,否则来不及。那时还没正式排练,导演蒋维国远在伦敦,我们通过视频聊剧本。《父亲》属于演员一看就知道非常难演,又非常喜欢的剧本。好的剧本写出生活的深度,看到人性、生存状态、人与人的关系。背台词搞得我很乱,我又想理解它,强迫自己背背背。虽然辛苦,但我必须承认,这是吸引我继续战斗的理由——必须完成这个演出。
 金士杰在排练
金士杰在排练
上观新闻:阿尔茨海默病的关注度近年与日俱增,这是吸引您演出《父亲》的原因吗?
金士杰:我不觉得《父亲》针对阿尔茨海默病。作为演员,我更关心作品本身。话剧定名为《父亲》,为什么电影译名要加上“困在时间里”?这个定语我不太愿意接受,我接受的只有“父亲”两个字。当然,了解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群很重要,他们值得被认识、被关心。
弗洛里安·泽勒写了三部曲《父亲》《母亲》《儿子》,不只是个人故事,也不是探讨特殊病例,而是讲一个病态的家庭。我读《母亲》《儿子》读得都快生病了,一边读,一边惊叹于泽勒的才华。他的笔像解剖刀,鲜血淋漓,弹无虚发,越怕疼的地方,他下刀越狠。我不能停止读下去,读完之后,又有好多天不快乐,再想想再翻翻,情绪冷凝,好滋味这才慢慢浮现。面对残破的生命本身,泽勒诚实、大胆地描述着无可救药的苦。相比《母亲》《儿子》,我感受到泽勒对《父亲》的温暖,很喜欢父女之间拉扯的过程。
上观新闻:安德烈年纪大了之后失忆失智,让不少人觉得晚景可怕,您怎么看?
金士杰:人如果不会思考,没有记忆,只剩下躯壳,我们勉强称之为人。我妈妈103岁了,我也必须面对她已经不那么清醒的现实。很多文字挖掘人与记忆的关系,《父亲》讲久病床前的故事,安德烈与女儿,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守在床边,两个人各自在想什么?我无法说,他们谁对谁错,每件事都充满复杂性。安德烈与女儿想辨析好坏对错,但没法分清,他们的对话不在一个频道上,谁都不好受。看完《父亲》,观众会发现,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每个家庭,快乐又残酷。
我想让观众在悲伤中感到快乐
在舞台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里,金士杰饰演患有渐冻症的教授莫利。2012年,他凭借该剧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壹戏剧大赏最佳男主角奖。“这出戏有长者的风范,剧情背后仿佛有一双和蔼可亲的手,温存地抚慰人世间的我们,鼓励我们、挑逗我们、逗乐我们也警告我们,帮我们抛开生死,拥抱世界。”
《父亲》中,金士杰再次饰演走向生命终点的人,他想让观众在悲伤中感到快乐,“我要让观众由衷去笑,别感觉到我在逗他们笑,我不能耍宝。每天,我都在这样的斗争中”。


上观新闻:《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也是久病床前的故事,《父亲》与之相比,有什么异同?
金士杰:莫利教授的渐冻症,慢慢失去的是肢体功能,他的记忆清晰无比,清醒着走向死亡。《父亲》是另外一种体验生命的过程。人一旦老去,就要面对不断失去,最后剩一口气,然后这口气也失去了。生活的内容越来越少,越来越够不着,这是必然的生物现象。
对于《父亲》,我会想,失去有什么可悲伤的?这是一出喜闹剧。对于莫利教授,我有类似态度,我很喜欢充满死亡、集欢笑与悲伤于一体的戏。观众在看戏时不时发出笑声,我听着非常舒服。我就是冲着这些笑声接的戏。
观众为什么在演员没有喜剧表达时笑?可能渐冻症的症状本身让人笑。很久之前,我和赖声川合作《摘星》,讲述心智障碍的人们,他们二十多岁了,智力停留在三四岁,那时也有观众在笑。《父亲》也是残忍又让人笑的戏。我偷偷想象观众的画面。在安德烈的病床边,观众们会笑吗?安德烈很认真地说自己是小狗,如果他只有三岁,人们觉得他好可爱。但他已经老了,观众会觉得他可笑吗?
上观新闻:有些演员不喜欢突如其来的笑声,他们认为,这是观众没有看懂剧情,对舞台不够尊重。
金士杰:我们没有刻意去搞笑,观众的笑声却油然而生。我作为演员有时困惑,是我解读错了吗,他们在笑什么?渐冻症让莫利教授无法自如行动,把一桌饭菜统统都打翻了,观众笑他惨状。安德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迷失在时间中,上一秒他深爱着女儿,下一秒就在问这个女人是谁。观众很残忍,一边看一边笑出声,这可能是编剧希望的事,把笑和悲伤融合在一起,比只哭或者只笑更高明。
上观新闻:田水在《父亲》里饰演您的女儿,她有至亲患阿尔茨海默病,这对她的表演有帮助,也为她的表演增加了难度。现实中亲朋好友的经历,会影响您的角色呈现吗?
金士杰:田水经历了那些事,所以剧本里有些字句像鞭子一样抽她的肉。我演安德烈,可以全身而退吗?我在努力追求角色的状态,而不是他的病理。生活中健忘,我们会着急、会自卑,害怕别人的眼光。安德烈健忘,没有挣扎,没有伤脑筋,忘了就忘了,反而是他身边的人担惊受怕。安德烈知道自己在生病,他很倔强,嘴巴不服输,嚷着不需要家人照顾,其实他担心船要沉了,老鼠一个个开始逃。
《父亲》讲述发生在父女之间的拉锯战,安德烈寻找依靠,女儿安娜挨了他最多的骂声,最被嫌弃,他又离不开女儿。这挺像一个人面对世界的关系,我们爱的永远是远方,而不是眼前人,远方总是好的。
 金士杰与田水
金士杰与田水
 金士杰与田水
金士杰与田水
上观新闻:听说您发了一集纪录片《前浪》给田水,那集讲到儿子把父亲送去养老院,他安慰自己,父亲在养老院常和老太太跳舞,很开心,一切都挺好。
金士杰:要不要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送到养老院,这是家庭会议可以决定的事情,但是有的子女永远都跨不过那一关。跨过去的话,有人会一辈子责怪自己,哪怕老人走了之后很多年,他/她还在自责。
安德烈是坏人,女儿安娜是好人,安德烈不正常,安娜正常,如果那么容易下结论,《父亲》算不上好戏。要是安德烈从头到尾都讨人嫌,戏剧效果并不好。《父亲》好就好在复杂性,我的责任是寻找复杂的一面。观众站在女儿安娜这边,还是愿意为安德烈说话,我希望他们的判断不断摇摆。儿女并不是不孝顺,而是做不到。安娜眼看着父亲症状越来越严重,照顾不了他了,台词是“你坚持不用护工的话,我就只能……”她说不出口,其实就是“我只能把你送到养老院去”。
我的爱的方式就是难缠
《父亲》正式演出了,金士杰每天依旧想着打磨。用他的话说,只有守着自己表演的秩序,才能让安德烈这个失去秩序的人物立住。
在一场安德烈与家人的餐桌戏上,金士杰需要知道,“这里是不是我最认真吃饭的地方”。他还为同事们操心。有一天半夜惊醒,想着饰演护工的青年演员贺梦洁在排练厅笑不出来,“是不是安德烈的踢踏舞跳得不够花哨?”看到贺梦洁笑了,又有一种老师见证学生成长的欣慰,觉得是“脑袋瓜里疏通了一些戏的态势”。
“我发现有好多功课藏在剧本里,就挺兴奋的。”金士杰表示,“说累也不累,每天都有新发现,这个事挺好玩。”同事们也早习惯了今天排完一段戏,第二天金士杰说,可能还是不够好,我们再排一下。
 《父亲》演出结束,金士杰被观众团团围住 网络截图
《父亲》演出结束,金士杰被观众团团围住 网络截图
上观新闻:六年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开始筹备《父亲》,向您发出邀约。这次来上海,首次与祖国大陆剧团合作,您的感受如何?
金士杰:上话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大家都很有趣、很可爱、很朴素、很傻、很认真。我有“挑食”的习惯,只有几个舞台剧导演的工作方式我可以接受。后来年纪大一点,成了家,我更不喜欢出门了,这一次接《父亲》真的是破天荒。
剧组很有意思,蒋维国导演集合的演员代表了不同风格,跨度还挺大。我每天拿什么更好、更准确的表演给到对手?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产物,而不是某几句精彩的台词而已。我忍不住笑地跟他们讲,我更爱他们的话,应该再发挥多一些,更“难缠”一点。我的爱的方式就是难缠。如果给我的东西不真,我又怎么说得出来真的台词呢?
上观新闻:您在表演时非常强调“真”。
金士杰:我在大学当老师时,每次回家,就是下课。作为演员,我没有下课的概念。这句话没有说成,我就要把它说成,再一看,时间已经到了半夜了。我有一种辨别“这个词儿是真是假”的能力。我不能接受台词没有说成我自己的话。不成功的话句,还在空中飘来飘去,我能舒服吗?只能继续去想,找源头、做功课,这不叫认真,这是演员必须面对的。
上观新闻:您的台词非常有个人特色。您是属于有天赋的人,看了剧本,理顺角色情感,瞬间能想到如何去处理,还是每天在家悄悄练十几遍?
金士杰:两种情况都有过,有没有天赋,我答不出来,我没有办法那么客观。但是表演要练习,像上课一样。我无论当老师还是当学生,都要求一句台词有多种操练法。最重要的是,我在演的时候,一定把自己置身于当下的生活现场去说。
我曾经被某些导演指出“太演了”,或者说“我们再来一次”。我要追求没有演戏的感觉,自然点。我会想象某种生活场景,有生活对象、生活氛围,这能帮助我找到事先不太能预知到的表达方式。比如《父亲》里的安德烈,我想起了朱自清笔下的父亲,蹒跚买橘子,一下子刻画出这个人的主题。安德烈自私,锱铢必较,剧中充满有趣的小题大做,就像我们每个人在某一件事情上过不去,就会越来越纠结。
上观新闻:您有什么增进演技的秘诀吗?
金士杰:我不能为镜头服务。有时候,我赶快把生活里我的家人、我认识的谁谁谁以及某些时候的我调动出来,洗掉眼前的摄影机,把剧烈的身体反应通通取消,回到生活这件事,最悲伤时,最愤怒时,生活里的那个我或者他是怎么做的。
我经常看纪录片、看新闻,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作表演参考。这样的研究充满乐趣。观察纪录片、新闻里的人如何与别人握手、微笑,我怎么就没想过这样演呢?有很多这一类教材,至于我的乱枪有没有打中鸟,我不想要负完全的责任,我只喜欢保持这种趣味,给自己挑战。
我的童心还在
金士杰并非戏剧科班出身,从屏东农专畜牧科毕业后,他在牧场待了一年半。1978年,金士杰离开牧场去台北寻求表演梦想。这一年,他创作了自己的首个剧本《演出》,出演了秦汉、林凤娇领衔的爱情喜剧片《我踏浪而来》。
1979年夏天,金士杰与同伴成立话剧团体“兰陵剧坊”。次年,他根据传统京剧《荷珠配》编导话剧《荷珠新配》首演,兰陵剧坊名声大噪。他还是《暗恋桃花源》里的第一代江滨柳。
从历史人物到贩夫走卒,金士杰享受塑造角色的乐趣,获得第28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第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从艺46年后,他依然把“童趣”视为工作的最大动因。
 金士杰在北京国际电影节 新华社发(李芳宇 摄)
金士杰在北京国际电影节 新华社发(李芳宇 摄)
 金士杰与丁乃竺在上剧场,他们是《暗恋桃花源》第一代江滨柳、云之凡
金士杰与丁乃竺在上剧场,他们是《暗恋桃花源》第一代江滨柳、云之凡
上观新闻:回顾“兰陵剧坊”当年引起的轰动,您怎么看?
金士杰:40多年前,“兰陵剧坊”起步时,观众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小剧场。“兰陵剧坊”一步步长牙齿、说话,摸索新的方向,有表现主义的,也有荒诞派的,其实是不满足于所谓的老派话剧竞争,不满足于单调的口味。我想建立某种实验剧场,建立一种童趣。
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专家,也不太追求专家的东西。我一直喜欢玩,东张西望,去纽约、伦敦、东京剧场一看,哇,有这么多东西,就开心地跑来跑去。现在年纪大了一点,我的童心还在,东瞧瞧西看看,只是活动力比年轻时候低一点。像蒋维国导演,还有弗洛里安·泽勒这样的编剧,他们在古典主义戏剧中找到许多新招,我喜欢这种方式,心中的童趣可以“得逞”,每次登台像在经营充满幻觉的舞台。
上观新闻:40多年的演艺生涯中,您受到谁的启发比较大?
金士杰:我学戏剧时,有老师出题,让每个学生说一句句子,生活里的句子。我觉得很简单,找了自以为有趣的话。结果老师总不让我过关。他让我回忆说这句话时刚刚做了什么事,穿着什么衣服,一句话的练习持续了很久,我都觉得老师是不是故意找我麻烦。但是经过所有这些麻烦的过程之后,我再说那句话,自己都被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讲得这么好!当时激动的心情,我一辈子记得。我永远感谢那个戏剧课程,让我这一辈子有了一个有趣的追求。
上观新闻:在上海工作之余,您如何度过,去看自己演出的电影《默杀》吗?
金士杰:我没有时间看电影,心里都想着未完成的演出。我没有预备过离开家那么远、那么久,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也渐渐老迈了,本来我应该更保守一点,增加在家时间,多陪陪太太孩子,不轻易出门。
我在上海演出的尾声,家人会来跟我相聚。之前我没让他们来,一是小孩要上课,二是排戏中,他们如果在,我没法专心。家里人一出现,我就有事要干,有话要说,心思没法全放在排练上。我希望,除了排练,生活中没第二件事。自己拿块肥皂蹲在地上洗洗衣服,一边洗一边想台词,不是很好吗?我好久没干过这种事了。
 金士杰在排练
金士杰在排练
金士杰:兰陵剧坊创始成员,长期从事舞台剧表演及编导工作,获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壹戏剧大赏最佳男主角奖。
舞台作品包括《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暗恋桃花源》,编导、出版《金士杰剧本I》《金士杰剧本II》《金士杰剧本III》,影视作品包括《棋王》《我可能不会爱你》《贞观之治》《绣春刀》《师父》《剩者为王》等。
栏目主编:施晨露
本文作者:诸葛漪
图片来源:《父亲》图片,王玉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