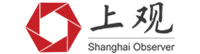初秋的一个周末,天色澄明,暑气渐敛。
马鹤虎和妻子又出发了。这一趟,他们要去往上海西北郊,寻找五棵三百多岁的古树。
在今天上海境内,一共生长着1886株古树名木,按照有关条例规定,每棵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即称古树,由绿化部门统一编号。过去三年,年近六旬的马鹤虎和妻子张咏梅相携,几乎走遍上海市郊的所有角落,寻访到上海市境内近300棵古树。
寻树途中,苦乐相依。他们将种种见闻与心情,悉数收入一札古树寻踪笔记。这是部一五一十、饱含情感的寻踪笔记,也是份近乎田野调查式的、用双脚踏勘而得的古树生长档案,记录着一个普通市民对古树最朴素的观察,以及观树刹那转瞬即逝的心境。
古树有时在乡野,阡陌相连,炊烟氤氲,流浪的小狗一路尾随;有时在古庙,木鱼声声,香火缭绕,守庙老人悠悠吐露些往事。
爱之深,痛之切。一路上,夫妻俩无数次为古树生命力之旺盛而动容,也为长势不振、命运堪忧的老树而揪心。
“在我看过的树里,有的保护得很好,有的一般般,有的很可怜。古树在这里生活了几百上千年,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能好好对待它,心里真的过意不去。”马鹤虎说。
2023年11月,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文,要求做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古树名木保护工作。这份文件还特别提到,古树名木“不仅是自然生长的树木,也是与文物建筑、石窟石刻、遗址墓葬等共同承载悠久历史传统、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活文物’”,鼓励开展“对古树名木文化内涵、历史价值的研究和必要的展示阐释”。
“我们总是很快,而它们一向缓慢。如果你正过着二倍速的人生,不如,去看一棵树。”今年9月,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举行,主题纪录片以此为结语。
大树沉默不语,却收容着人世更迭的秘密。那些穿透历史尘烟、散落在我们身边的古树,如今还好吗?
或许,我们可以从此刻开始,随马鹤虎夫妇的古树寻踪笔记,重新发现和凝望每一棵长久注视人间的古树——了解“他”的过去,追问“他”的境遇。
 马鹤虎和张咏梅夫妇在树下。
马鹤虎和张咏梅夫妇在树下。
一
从上海市区驶出,约一小时车程后,车窗两侧的景色逐渐由城市转为阡陌田野。秋风起,正值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
“是那棵吧?”
远远地,眼尖的马鹤虎和张咏梅已发现了古树的踪迹。
顺着他们所指的方向,极目地平线远处,果然有一朵圆弧形的树冠,在连片农田、屋舍和树丛之间,微微冒出点头。
走近看,这是一对300多岁的夫妻树,临河而立,与一座土庙相伴,树下铺满往年的落果。“雄树可能多年前遭过雷击,个头矮一些,但主干附近生了蘖枝,死而复生。”马鹤虎看得仔细。
 编号0148、0149的一对夫妻树,与土庙相伴,临河而立。周丹旎摄。
编号0148、0149的一对夫妻树,与土庙相伴,临河而立。周丹旎摄。
在两人寻访过的所有古树中,这对夫妻树长势还算不错。马鹤虎心情松快,随手拾起一把稻草,小心将古树身份牌擦拭干净。
寻踪笔记中所收录的100棵古树,夫妻俩几乎都这样亲眼看过、亲身踏勘(除了几株非公共绿地的古树未能得见)。寻树不易,唯一的依据是手头一本2002年出版的古树名木手册。二十多年已过,城乡风貌大变,大部分地址淹没在城市变迁的洪流中,走上一天一夜寻而不得,也是常事。
好在边走边问,想见的古树,几乎都见到了。按照生长状况和周边环境,马鹤虎将这100棵古树做了个分类,“大约有31%的古树生长得不错,51%的古树长势环境一般,还有约18%的古树长势到了堪忧的地步。”
这是来自一位外行人直观的经验判断。
在2016年的一篇科研论文中,研究团队调查了上海市2409棵古树名木(数据包含树龄在80年以上、100年以下的古树后续资源)的生长状况,认为其中约四成树木生长良好,四成树木生长一般。生长衰弱和濒危树木约占7%。
两者评价标准或许不同,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生长良好的古树数量不到半数,还有部分古树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马鹤虎说,最让人心焦的是,不少古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村庄消失,变成高楼、工厂,留给古树的生存环境越来越逼仄。”
位于宝山区的0090、0091号古树,树龄400多岁。三年前的冬天,马鹤虎携妻子寻访到此,发现“道路的拓宽把两株古树硬生生挤到一起”,树干几乎贴墙而立,密集的电线从树冠中横穿而过。据资料记载,两株古树似为大场古镇东岳王庙的“遗物”。
回金山老家途中,马鹤虎多次造访一棵850多岁的0013号古树。这是金山区最老的古树,称得上“金山树王”。古树所在地,曾是西观音堂遗址,资料记载,“西观音堂,也称西来庵,始建年代不详,元至正年间重建。”马鹤虎见到这棵树的时候,它正被厂房包围,与最近的建筑相距不足5米,生长环境狭小,长势较同龄的古树更低矮些。
 “金山树王”被厂房包围,长势较同龄的古树更低矮些。受访者供图。
“金山树王”被厂房包围,长势较同龄的古树更低矮些。受访者供图。
有一回,马鹤虎沿途打听一棵古树的确切位置,被一位当地居民误认作工作人员,“他很急切,一路跟上来,说这棵树是陪伴他祖祖辈辈长大的。小时候,古树还很茂盛,现在病恹恹的,长势不如从前了。据他说,古树周围的一圈墙体影响了排水,遇到台风天、暴雨天,树根附近容易积水,来不及排出。长此以往,古树经不起折腾。”
与马鹤虎的观察一致,前述论文指出:古树名木作为自然系统的本底标志物,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着生存危机。
现行的《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要求古树名木保护区应“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五米”。而据上述论文2016年的调查数据,当时上海有约89%的古树名木处在规划集中建设区内,“1/3的古树名木实际保护区半径只有5m,保护半径较小;1/3的树木距离建筑小于5m,非常不利于保护;11%的树木周边存在不透气铺装,直接影响古树名木的生长”。
在机器与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古树沉默地栖身于城市化建设的缝隙里。
二
与空间退让相伴随的,是某种传统的消散。
一棵古树,千百年来挟带着怎样的风霜雨雪?来往于城镇、乡野之间,马鹤虎发现,能说得清古树故事的人在一点点流失。
园林绿化部门为每棵古树立有身份牌,展示着编号、树种、保护级别等信息,还留下一个可扫描的二维码,但无论是保护牌还是二维码界面,都并未对古树的历史文化背景做进一步介绍,让人“求知无门”。
 古树的身份牌上,除了编号、树种、保护级别等信息,看不到更多故事。周丹旎摄。
古树的身份牌上,除了编号、树种、保护级别等信息,看不到更多故事。周丹旎摄。
每每站在树下,马鹤虎心中总是升腾起一种莫大的好奇——静默无言、穿梭时间的古树,是什么来历?它见过什么人、又经历过什么事?
寻树途中,夫妻俩留心访问乡里,希望收集更多的古树故事。
不过,古树周边总是冷清。但凡问起老树的种种,年轻人多摆摆手,村庄里更是几乎不见年轻面孔。一棵老树,围坐几位老人,成了寻树路上最经典的一幅画面。只有老人还留守在树下,也只有老人才道得清原委。
有年初冬,马鹤虎夫妇和外甥一家赴松江探访上海0014号古树。有位孵太阳的长者,主动来搭话。
“大哥告诉我,他从小在树下长大。这个小区过去属于松江区仓桥乡彭家生产队,最早的时候还有座和尚庙。古人喜欢在庙里栽树,有树便有庙。他说,这棵老树有个特点,树上长树。什么是树上长树呢?因为树很大嘛,长年累月,种子飘来、鸟儿衔果子过来,树上又长出好多别的植株,和老银杏树生在一起了。”
当日,银杏叶落尽,一地金黄。老人叼着一根过滤烟嘴,时不时挥动双手上下比画,如数家珍地谈着古树的种种传说与变迁,腰间别的一串钥匙随之“叮铛”作响。
马鹤虎想起来,自己的童年里也有棵老树。
儿时的他,在金山廊下的六里塘河畔长大。走出老屋,河对岸立着一棵老银杏树,树皮粗糙,主干粗壮,童年的马鹤虎与玩伴三人都难以合抱。
“呜——呜——”
每天清晨,日上三竿,从浙江平湖始发的“小班轮”准时从门前河道驶过,拉响汽笛。男孩睡眼惺忪,母亲已在门外用金山话声声唤他起床。六里塘河畔,老宅、土庙与老银杏树的画面,在他记忆里久久定格。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古树根系被不远处养殖场流出的污水泡烂,在某个台风天里轰然倒塌。
“倘若这株古银杏树仍然‘健在’,它就是我记录的第一棵古树,那有多好。”
后来,马鹤虎做了远洋海员,离家越来越远。海上茫茫、无所依凭,日思夜想的是港口的航标。漂泊半生着陆后,他开始带着妻子孜孜不倦地寻树。古树根深不移,如同游子的航标,“朝着古树的方向走,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古树周边总是冷清,一只树叶丛中取暖的小狗一路尾随,目送马鹤虎夫妇离开。受访者供图。
古树周边总是冷清,一只树叶丛中取暖的小狗一路尾随,目送马鹤虎夫妇离开。受访者供图。
房前屋后的古树,是人们的乡愁所系,也是一座城市历史文脉无声的见证者。
上世纪80年代,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先生造访位于嘉定的0001号古树时,曾留下绝句:六朝文物越千年,古寺禅林尽荡然。银杏一株今尚在,从知润物有渊源。
古树是扎根城市的故人。生活在今天上海境内的1886株古树,储存着这片土地沧桑流转的生命片段。
嘉定的0001号古树,树龄1200余年,大约植于唐德宗贞元年间,所在地曾是老顾庙旧址。老顾庙,相传是为纪念1400余年前长居上海的南朝学者顾野王而建。
奉贤的0015号古树,与三女冈遗址相伴770余年,相传这里曾埋葬着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三个女儿,王安石有诗云:三女共一丘,此憾亦难平。音容若有作,无力倾人城。
上海现存最古老的牡丹,是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为贺好友金学文乔迁新居,赠予金家的礼物,两人曾同读于松江叶榭水月庵学堂。这株“江南第一牡丹”,金家后人守护了它近五百年。
千百年来,古树迎来送往、坐看云起,见证一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承载着超出个人生命尺度的历史记忆。
“相比于古树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我们对它的挖掘和了解都太少了。”马鹤虎回忆,在他们所到之处,大多古树无人问津,人们对近在身边的“活文物”似乎熟视无睹、所知甚少。他担心,再不抓紧收集和挖掘古树故事,随着老一辈人渐渐离世,这些口耳相传的过往终有一天将湮没尘埃,乡土与历史记忆也将随之消失。
三
翻阅旧闻,古树保护并非新鲜事。上世纪80年代,古树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一度十分尖锐。
当时,有上海本地报纸撰文指出:古树名木,现在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一些单位向古树争土地,靠近古树造房建屋,甚至锯枝、剥皮、砍伐,使许多古树奄奄一息。
有读者多次给报社写信,痛心疾首地呼吁:树龄八九百年的古银杏树,多年来无人认真管理。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切实地把这种难得的古银杏管起来,不要因为我们的过错而让古树名木雕朽。
时任市政协副主席赵超构,在一次公开会议上不客气地说:让这些传了几代的“文物”死在我们手里,子孙后代会笑话我们没有知识,不懂文明。
1983年年中发生的一件事,进一步刺激了公众敏感的神经。为兴建工厂,吴淞地区投入巨额,搬迁了一株七百多年树龄的古银杏。然而,古树移栽后,生命体征持续恶化,最终没能保住性命。
抢救古树,到了时不我待的地步。
1983年9月,上海在全国首开先河,颁布实施了《上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这是全国首部古树名木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十余年后的2002年,《规定》修订后更名为《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将树龄为80—99年的树木列为古树后续资源,纳入保护范围。
“上海为古树名木立法后,在全国起到一定示范作用,许多省市都跟进颁布规定、条例,古树名木保护开始有法可依。”一位退休前长期从事古树保护一线工作的专家介绍,后来上海又相继推出古树认养、古树公园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客观上说,上海的古树保护工作在全国走得是比较前面的。”
四十余年过去,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观念上,古树保护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城市规划建设进程中,地铁二号线建设、东方体育中心建设等重大市政工程都曾为古树“让路”。
 2010年,东方体育中心场馆建设位置整体向北移动,为古树“让路”。受访者供图。
2010年,东方体育中心场馆建设位置整体向北移动,为古树“让路”。受访者供图。
既然如此,为什么从实际观感来看,古树保护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紧张依旧?
一部分,是历史原因。一些古树周边工程建设年份较早,未按照后来《条例》的标准划定保护区域,后期也没再做修正。“对于这类情况,要尽快想办法恢复它的生长环境。”
从更大范围看,只要城市规划建设、城市更新还在持续推进,就无法避免与古树保护产生冲撞。
“建设让路”还是“古树让路”?按理说,这是个不再需要探讨的问题。按照《条例》规定,一级保护的古树禁止移植,二级保护古树因特殊原因确需移植的,需要报市政府特批。也就是说,古树能不移就不移。然而,一些地方为顺利推进土地开发建设,绕过《条例》正常程序,强硬挪树的现象依然存在。专家坦言:“到今天,这种事情也比较少了,但是一旦发生就很伤人心。”
再进一步说,古树保护是项系统性、过程性的工程。即便将古树保留原地,开发建设还需遵循一系列具体的要求和标准,比如控制土壤标高、地下水位、光照和排水条件等。保留古树,又不做好科学的保护方案,与伤害古树无异。专家回忆,多年前,某地盖楼时,特意为避让古树“切了一角”,但盖起的新楼挡掉了阳光,又影响了排水,古树最终也没能保住。
“事实上,我们做建设区古树保护研究这么多年,发现最大的漏洞就是规划。不从规划源头抓起,在不知道有古树的情况下,土地先批掉了,建设单位在规划前期不知实情,后期改变方案比较困难,古树保护工作就会很被动。”
专家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把古树管理部门和规划管理部门统筹起来,将古树名木数据与城市规划数据对接起来,让新项目在规划早期就避让出古树的生存空间,实现从规划源头保护古树名木资源。
四
如今,距离上海出台全国第一部地方性古树名木保护法规,已经过去了41年。距离《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已经过去了22年。这份条例,至今仍是上海古树保护工作开展的最重要依据。
时代在变,我们的古树保护工作,是否又该站到新的起点上、凝聚新的共识?
2018年,有人大代表曾通过本报呼吁:“现行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的修订有些滞后,不能满足现实的管理和养护需要。”
古树名木的申报,是其中一个“漏洞”。该名人大代表指出,《条例》规定古树名木认定需树木权属人申报,可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部分单位、市民不愿意申报的现象,“他们害怕承担相应的养护责任和管理责任,不愿意上报。”不申报,就不能被认定为古树名木,也就无法按照古树名木的要求实施保护、落实责任,这是个恶性循环。
另一个问题,是经费。代表发现,《条例》并未对古树名木保护的养护定额和经费作出具体规定,“导致各区古树管理部门以及古树所在单位在古树名木的养护费用申请和管理保障上,无法与一般树木的养护费用加以区分。”
除此之外,公众对古树名木保护,或许还有新的期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读者在来信中提及:古银杏树与古寺庙建筑相得益彰,其珍贵程度,并不亚于寺庙大殿。
几年前,一份绿化行业报曾撰文指出:“提起古树名木,人们脱口而出的说法是活文物、活化石,可见古树名木是活的文物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古树名木是活的文物,有名更要有实。”
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古树,实际上兼具着生态、文化的双重性质。但也正是这种双重性质,让古树在历史文化层面的身份显得有些尴尬。
翻阅《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其中要求“加强对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应用科研成果,宣传普及保护知识,提高保护水平”,并未从历史文化层面对古树名木保护作出具体规定。
一方面,人们公认古树是“活文物”;另一方面,在保护性质上,古树却只被当作植物,主要由园林绿化部门从生态上予以保护,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开展研究。在实际操作中,管理部门主要承担植株养护的责任,首要考虑的是树的健康,而非文化留存。
在前文述及的古树保护专家看来,当下对古树名木文化价值的挖掘,还远远不够。“过去,古人是不会无缘无故种树的。一棵古树,千百年来见过生生死死,肯定是有故事的,要挖掘出来。现在到处是旅游热、文博热,没有的东西也要树一个,古树这样活生生在你面前的宝贝,为什么反而忽视它呢?”
国务院原参事、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盛炜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确立古树名木的文物身份、落实文物待遇,利于从根本上推动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从现实需要和长远保护来看,古树名木所具有的生态、文化双重性质,或应更好地被确认、体现出来。
值得高兴的是,有一些改变已经在发生。
前述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的通知,明文指出古树名木“不仅是自然生长的树木”,也是“承载悠久历史传统、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活文物’”。
通知还将“深化价值阐释”单列为一条,鼓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机构或管理使用单位开展对古树名木文化内涵、历史价值的研究和必要的展示阐释,鼓励在文物主题游径建设中统筹考虑古树名木保护与展示工作。
“现在越来越呼吁保护传统文化,古树也是传统文化呀,你说是不是?只是古树自己不能说而已,它们什么都知道,却说不出来,我们要去民间走访、采风、挖掘收集史料,帮助古树开口‘说话’。”张咏梅有种紧迫感。
尾声
寻树这天,我们要找的最后一株古银杏,藏在一座香雪庵内,背靠着鹤槎山。十多年前,香雪庵曾修缮开放,如今不知何故大门紧锁,从墙缝望进去,庵内已经荒废许久,古树也难以得见。
史料记载,古树所在的鹤槎山,自古是军事要塞,原为宋军抗金构筑的烽火墩,太平军与清军也曾在此激战。据说,山下银杏树上还留有炮火的残痕。900年鹤槎山、300年古银杏,见证了历史的烽火硝烟。当日,香雪庵外行人来往,对这山、这庵、这树熟视无睹。
马鹤虎凑近围墙的花窗,努力把目光投向古树:“古树是有灵性的,我来看它,它一定也在看我。”
返程路上,车载音响传出刘文正的《秋蝉》:
“总归是秋天,
总归是秋天,
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
莫教好春逝匆匆。”
又是一个新秋。马鹤虎惦记着,家乡金山那株古银杏树的白果将要落下,他要携妻子再去拾些新果回家。
 马鹤虎在捡拾白果。
马鹤虎在捡拾白果。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本文作者:周丹旎 何东
题图来源:李茂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