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国庆日定于7月14日,通常认为是旨在纪念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标志性时刻。然而,也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1880年法国国庆日选在7月14日,纪念的是1790年,而不是直接纪念1789年;换句话说,纪念的是君主立宪制得以登场的联盟节。如何理解上述观点之间的异同?阅读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科林·琼斯的专著《伟大民族:从路易十五到拿破仑的法国史》和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也许有助于揭开围绕法国国庆日起源的迷雾。
1789年:革命之日
“1789年7月14日的故事已经被写入每一本讲述法国历史的书中,而当天的核心事件——攻占巴士底狱的前因后果也无须赘述。”即便如此,科林·琼斯对巴士底狱的描述仍贯穿了《伟大民族》叙事的始终。这座始建于14世纪的军事堡垒,至18世纪已成为波旁王朝专制统治的象征。路易十四统治期间,170多名作家和书商被捕入狱,引发欧洲各国震动。启蒙运动时期,约6000本《百科全书》曾被扣在狱中禁止出售,博马舍的名作《费加罗的婚礼》在删除涉及巴士底狱等内容后才获准演出。旧制度的法兰西沉疴积弊,凡尔赛与巴黎的矛盾一触即发。
1789年5月5日,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博弈,国王于6月27日命令贵族和教士加入第三等级,但同时派遣军队进驻巴黎。7月11日,路易十六解雇财政总监内克的消息传至巴黎,财政改革方案的落空引发民众恐慌。出于保卫城市的需要,巴黎民众寻找武器弹药的活动演化成军事进攻。7月14日,起义军队转向巴士底狱,攻守双方激烈战斗,起义者释放了监狱内仅有的七名囚犯,并高举监狱长洛奈侯爵的头颅绕城展示。虽然路易十六当晚在日记中写下“今日无事”的字样,但他很快意识到“巴士底狱的陷落改变了一切”。国王于7月17日来到巴黎市政厅,确认了革命的成果。科林·琼斯写道:“当他戴上象征着和解之日的三色帽徽时,巴黎的红、蓝色衬托在波旁王朝的白色两侧,一个崭新的、社会与政治相互和谐的时代似乎正在开启。”
就在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次日,私人承包商帕洛瓦迅速启动了拆除工程,将一些石块作为“爱国纪念品”出售。帕洛瓦的行为获得了官方认可,这些石块还被加工成巴士底狱的等比例模型送往外省,助推了革命精神的传播。不过,旧制度的“拆除”和大革命的“构造”,远非一日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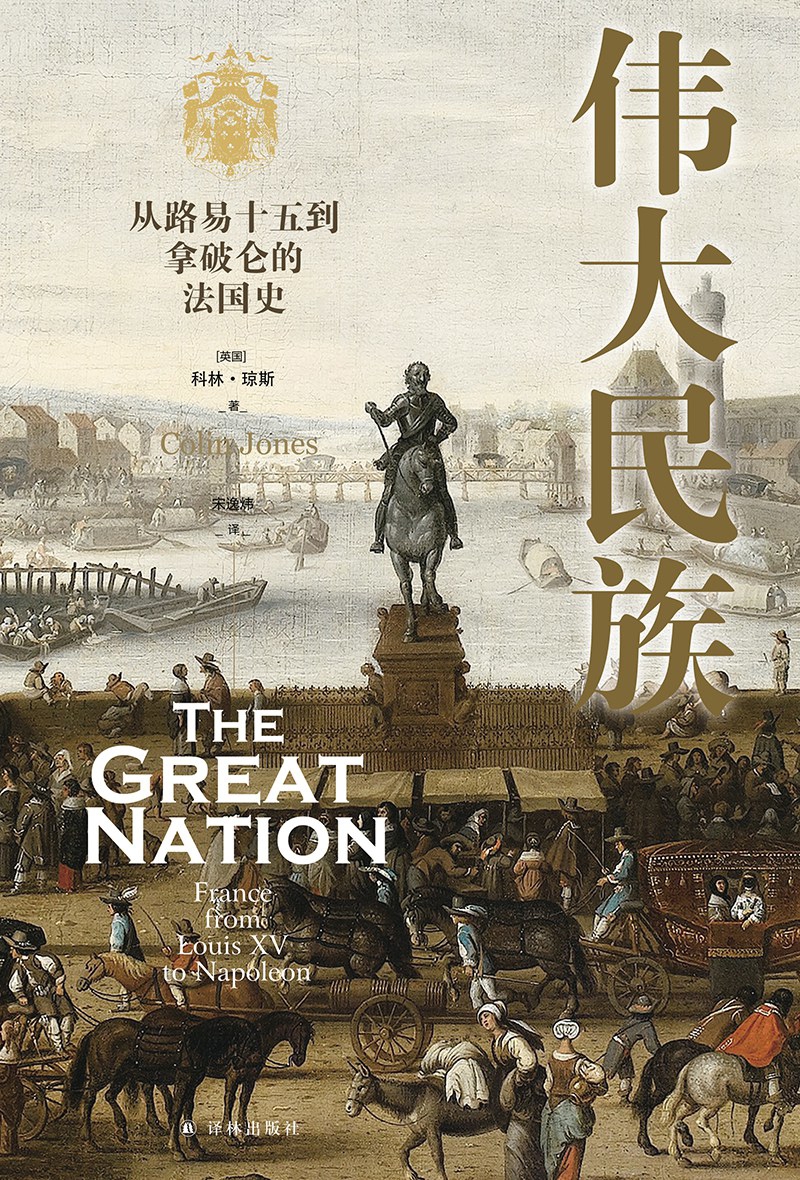 《伟大民族∶从路易十五到拿破仑的法国史》,[英]科林·琼斯 著,宋逸炜 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出版
《伟大民族∶从路易十五到拿破仑的法国史》,[英]科林·琼斯 著,宋逸炜 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出版
1790年:团结之日
在1789年底至1790年初相对和缓的环境中,崭新的公共精神融合了中央政府的推力和下层地方的活力。为了塑造国民团结的气氛和革命新人的典范,拉法耶特决定在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之际举行隆重纪念,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应时而生:“巴黎的战神广场上搭建起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剧场,25万巴黎市民在此见证了一场象征国民团结的庆典,活动的领导者是国王本人……1789年以前没有值得纪念的历史——在此之前的公共历史现在被认为仅仅是记载国王和教士罪行的编年史,而大革命本身的历史却得到了适当的纪念。”由此,节日文化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发明,推动了革命事业的普及,“见证了真正的爱国情感在基层的萌发,而这又与1789年以前公开场合的大众娱乐活动息息相关”。
科林·琼斯通过强调攻占巴士底狱的革命意义和1790年联盟节的团结作用,讨论了1789年的断裂与延续性,进而全面审视1715—1799年间的法国历史。据其表示,《伟大民族》的写作深受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转向”和政治史复兴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记忆之场’取向——采用由皮埃尔·诺拉普及化的术语,结合对过去痕迹的物质化兴趣,分析其在国民文化中的神话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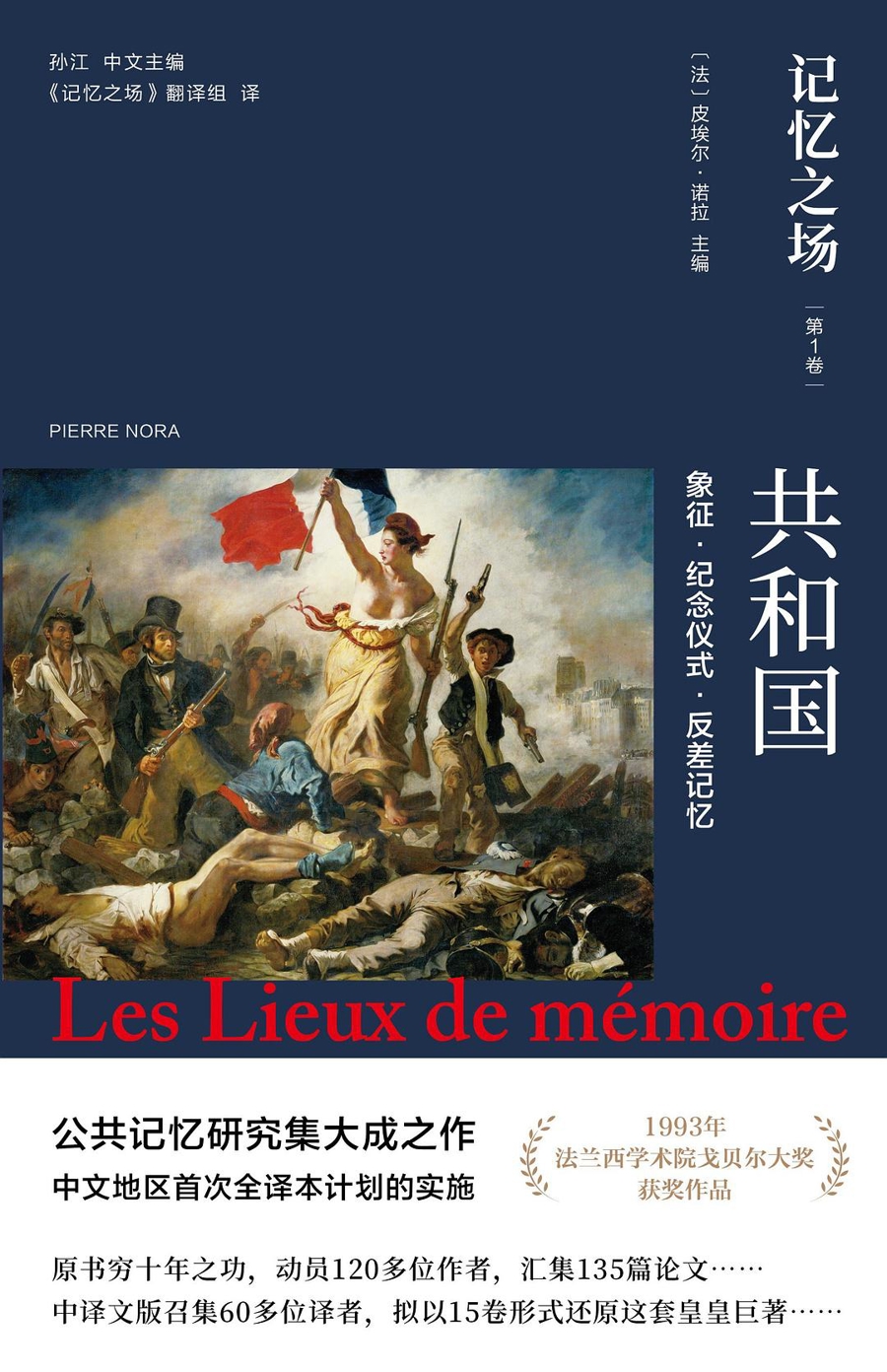 《记忆之场》第1卷《共和国》,[法]皮埃尔·诺拉 主编,孙 江 中文主编,《记忆之场》翻译组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
《记忆之场》第1卷《共和国》,[法]皮埃尔·诺拉 主编,孙 江 中文主编,《记忆之场》翻译组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
1880年:妥协之日
1984—1992年间,法国伽利玛出版社著名编辑皮埃尔·诺拉动员120位作者,汇集135篇论文,主编出版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著《记忆之场》。全书分“共和国”“民族”“复数的法兰西”三部七卷,并于1993年荣获法国最高国家学术奖。“记忆之场”是诺拉创造的概念,旨在考察不同象征符号与国民意识形塑之间的多重关系。由于7月14日之于法兰西现代国家的重要性,该条目被列入第一卷率先出版,文章作者是档案学家、时任法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
大革命以后的法国政体在共和与帝制之间跌宕起伏。1879年,共和派政治家朱尔·格列维当选第三共和国总统,如何通过纪念共同的节日达到凝聚共识的效用,成为全体共和派成员亟须面对的问题。当时,许多日期都被纳入讨论范围。例如,1792年8月10日,路易十六被突然逐出杜伊勒里宫,对这个日期温和派和君主派无法予以认同。再如,1792年9月20日和21日,法国取得瓦尔米战役的胜利并宣布成立共和国,但在此后趋向激进的革命未免惹人瞩目。至于19世纪的历次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带有鲜明的奥尔良主义倾向;1848年第二共和国的存续时间太过短暂;1870年第三共和国的成立背景是拿破仑三世的色当惨败;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者此时尚未获得全面大赦……都不足以令各方满意。由于维克多·雨果笔下“1789年,巴士底狱陷落,人民的苦难终结”“7月14日是一次拯救”“掀翻巴士底狱,人类得解放”的描述深入人心,共和派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选择了7月14日:“这个日期有两重意义,它既指攻占巴士底,也指联盟节,后者具有全民族团结的特征,因而能够去除前者的暴力和血腥色彩,能够比较方便地消除温和派的疑虑。”
1880年5月21日,来自巴黎的众议员本杰明·拉斯帕伊提出设立国庆日的议案。7月14日,各界代表齐聚隆尚赛马场,庆祝第三共和国的首个国庆日。然而,欢乐的氛围背后只是共和派与保守派的暂时妥协,这次官方庆典将宗教色彩排除在外。未来数十年内,敌视共和国的势力仍将对7月14日的历史地位发起挑战。
阿马尔维在《记忆之场》中详细梳理了7月14日从“狂暴之日到庆典之日”的流变,并不免遗憾地写道:“在7月14日被确立为国庆日百年之后,那些在戏剧性局面下曾赋予该节日独特光彩的持续斗争,在今天的法国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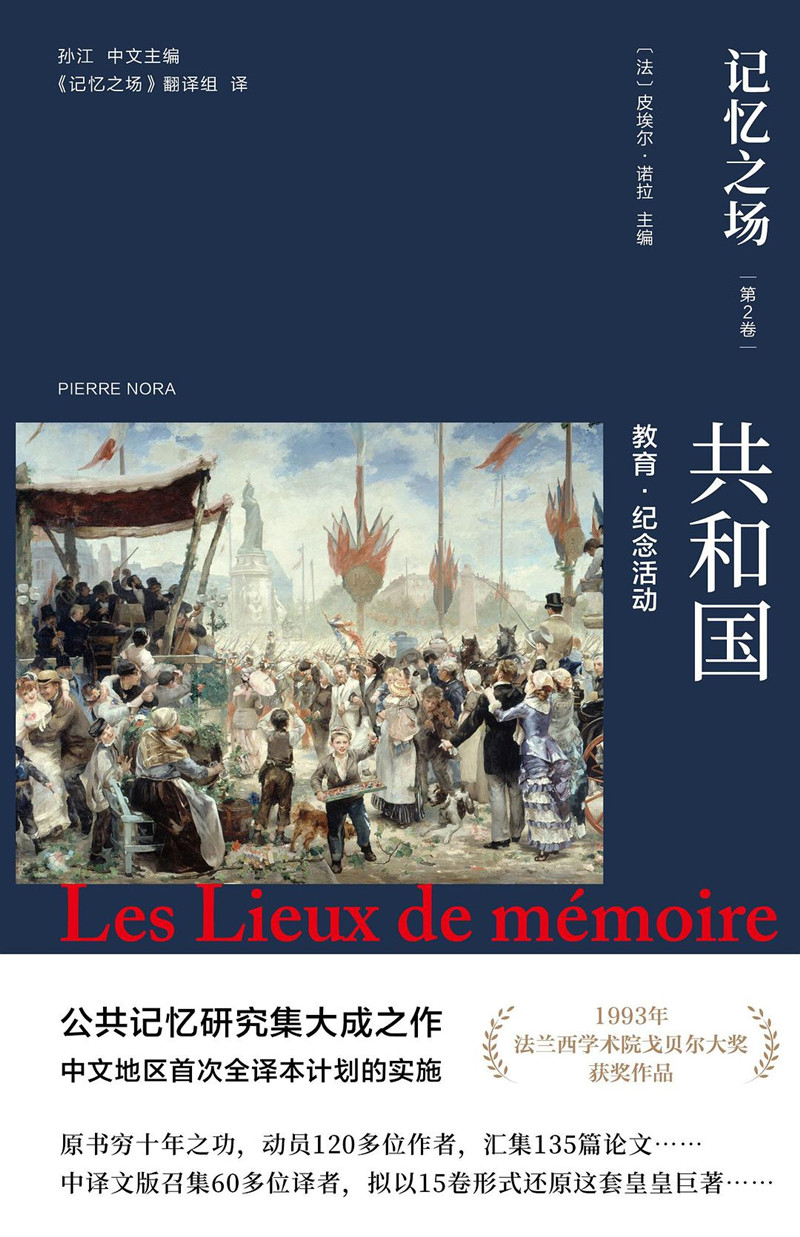 《记忆之场》第2卷《共和国》,[法]皮埃尔·诺拉 主编,孙 江 中文主编,《记忆之场》翻译组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
《记忆之场》第2卷《共和国》,[法]皮埃尔·诺拉 主编,孙 江 中文主编,《记忆之场》翻译组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
事实上,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正是《记忆之场》的主要特征。诺拉的初衷原是为了批判以往强调整体的法兰西历史叙事,却在有意无意间塑造了属于全民族的集体记忆。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参照1880年共和派达成的共识,得出一个相对模糊的结论:法国之所以将7月14日定为国庆日,既是为了纪念攻占巴士底狱的革命精神,也是为了纪念首个联盟节的团结氛围,其本质则是为了勾连从大革命到共和国的政治文化谱系。如果回到有关7月14日的“记忆之场”,我们或许会有新的发现:1789年的巴士底狱早已被拆除殆尽,如今只剩地铁站内的片砖只瓦;现在矗立于巴士底广场的七月柱,实则旨在纪念1830年革命;1790年举行联盟节庆典的战神广场,曾见证了1791年的血腥屠杀和1794年的最高主宰节;1889年大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法国政府在此建造埃菲尔铁塔,如今作为国庆音乐会和烟花秀的会场。1793年处决路易十六的革命广场,今天则是国庆阅兵式的检阅台;它的名字几经更迭,最终获得了一个看似和解的称谓——协和广场。
原标题:《法国国庆日的记忆之场:从巴士底狱到协和广场》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本文作者:宋逸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