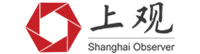你有没有在等待的那个人?早已离世的亲人,爱而不得的白月光,或是远离他乡求学的孩子。我们只要有所牵挂,便总会进入一个等待的状态。我们会等待一个迟早会归来的人,他可能是去上学的小孩,也可能只是出门买菜的爱人。等待之中,欲望和激情以不同方式在身体里弹奏乐章,而试图压倒诸如理性和道德之类的力量,我们明知不可,却心向往之。在这些繁多的等待现象后面,是否有一种名为等待的东西?它有意义吗?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简单的激情》则试图叩问其答案。《简单的激情》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我”和一个外国男人A.的婚外情故事。正如书名所暗示的,这本自传体式的小说并不试图展现一个爱情故事,而是试图探索欲望、激情在人身上不可克制地涌动。埃尔诺以近乎手术刀般精确的观察,剖开这个身体和意识交织的共存体。
在开始之前,埃尔诺要求读者首先进入一种“非道德”的等待:“这样的一种恐惧,这样的一种惊愕,将道德评判暂时搁置。”“非道德”要求我们暂且抛开我们对情感绯闻的道德评价,只是单纯去思考欲望和激情如何以一种不可控的方式在我们的身体里呈现。
这是一种怎样的等待?在这部作品里,首先是狂热的迷恋——“我也不愿意把精力转到别的事情上,而是只想等着A.。”在等待中,工作和生活原本的秩序被打乱,“我”的生活开始以另一种非理性的秩序进行。
这之后,是恐惧带来的后撤举动:“我”主动断联,甚至逃离到另一个城市佯装旅游而试图放弃等待。可是,等待从来不是一个人能终止的简单程式,即使试图逃离,欲望却愈演愈烈:“一种额外的支出,这一次是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支出了想象和欲望。”等待放大并投射了欲望,在这之中,我们甚至会认可疼痛。埃尔诺说:“我很习惯于在欲望与事故——要么是我引发的事故,要么我是受害者——或者疾病,总之是多多少少有些悲剧性的事情之间维持平衡。通过想象,审度我是否接受满足欲望有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习惯于用疼痛衡量爱意,连爱得死去活来、心疼这样的词语都要求代价。
可是,感情本就不是持衡的状态,等待的奇妙感觉会随时间消失。生活的秩序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中被迫重塑。逛街、做饭这些再平庸不过的小事,却维持并把握着秩序。“我”开始有些许迷恋起等待时的非常规体验,开始倒退性地回忆,但依然无法延长时限,无法自由地进入当时的奇幻状态……不过,埃尔诺给我们留了一个精致的彩蛋:“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回忆,写作给了“我”一个进入等待状态的契机,从而变相地延长了“我”的等待。
至此,埃尔诺的等待才完成了一个闭环,但是,埃尔诺对它的刻画却不止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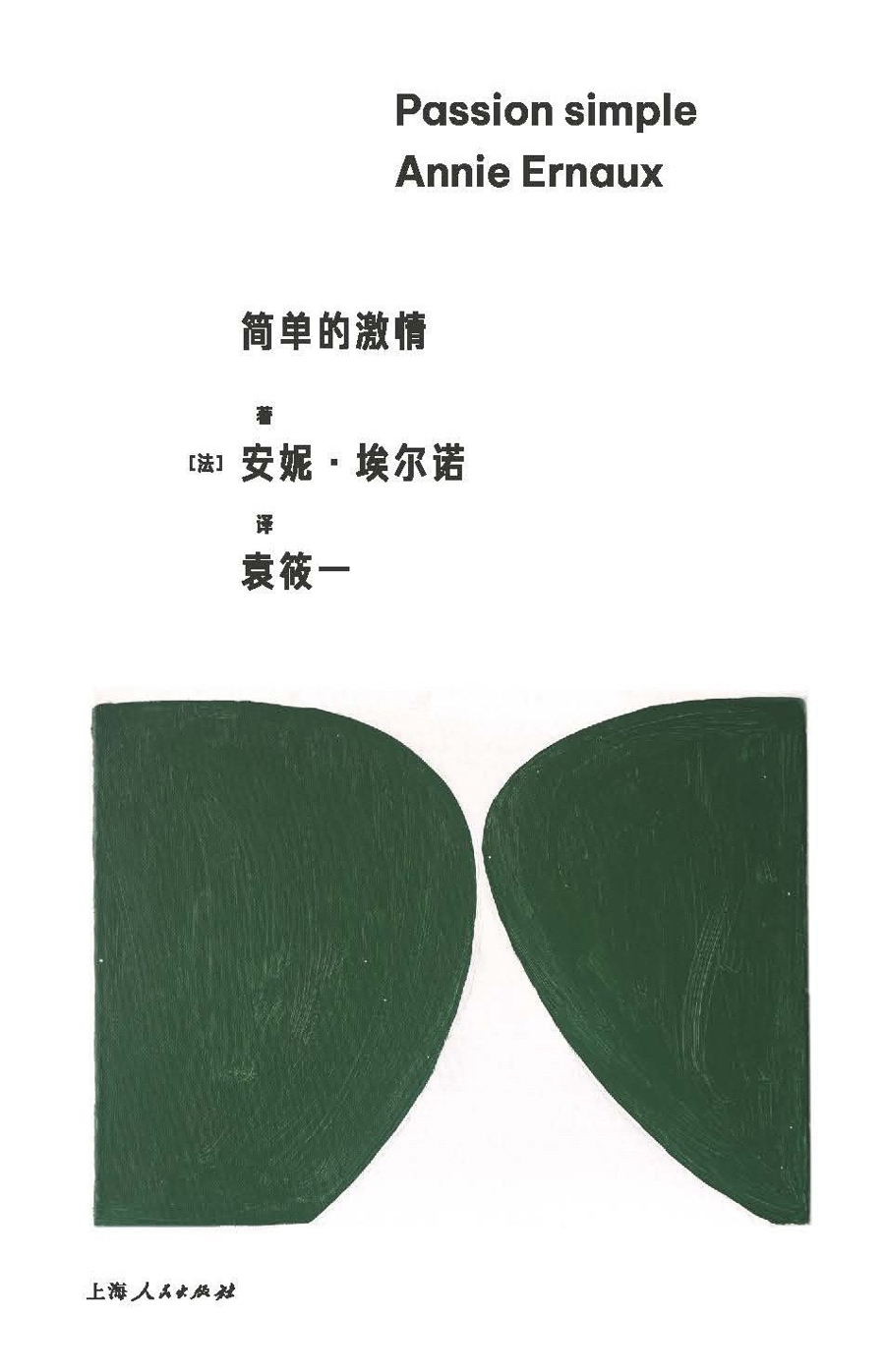
埃尔诺还试图叩问等待本身的意义:是否存在为了等待而等待?看起来抽象的问题,实际上却细碎地蔓延在我们生活的角落里:“我也不愿意把精力转到别的事情上,而是只想等着A.:不要破坏我的等待。”我们明知道某人某事尚未到来,但却沉浸于期待、希望和欣喜中,以至于不愿意做所谓的正事,我们守护的不是“某个人”,因为他尚未到来,或永不在场,我们守护的其实就是等待本身。
为什么要守候这样一段缺席的时间?埃尔诺尝试给出一个答案:在等待中,我们自由地构造属于“我”的想象叙事,创造“我”的故事情节。故事和情节的缺失给了我们巨大的自由,来构造这个世界最浪漫的事:离去的奶奶在想象中蝶变羽化,不再严厉;爱而不得的人在叙事中剔除桎梏,恒久温婉而美丽……等待让现实撕开了一个裂口,我们得以暂别现实的冰凉和残缺,只保留自己喜欢的那一面。
等待敞开了一片自由之地,在这里,我们放肆地利用它,抵达一种魔幻甚至迷狂的状态。随时随地,“在区域快铁、地铁、等候室,所有允许我神游的地方,只要一坐下,我就进入了有A.的梦幻。”它所给予的极大自由,不只给我们回忆的空间,更多是创造的空间,去想“如果……”;去想“好像……”:如果奶奶还在身边,她那时好像向我挥手……那些和现实沾边的想象,不是为了索求现实的明证性,也不是为了求证真实性,而只是因为通过现实,我们更方便去进行想象。
由此,埃尔诺从对等待本身的发问开始,到对对象的缺席和在场的思考,再到对想象叙事、自由和时间的思索,勾画了对等待的丰厚体验。
在《简单的激情》中,等待这样一个简单到甚至不会让人自发反思其含义的词,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对不同的等待情形的刻画,一步步揭开了作者对激情和欲望的思考。
我们为何而等待?无意义和目的的等待是否具有价值?诚实地说,埃尔诺实际上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理论上的阐释,她并没有给我们答案:“我不想解释我的激情,我只是想呈现它。”但实际上,这种力图对事实进行描绘而不评价的写作方式给读者敞开了广阔的理解空间。作为一个读者,我也试图在埃尔诺的刻画中,找出自己的答案。
关于等待,想必很容易想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等待的是不可知的对象——戈多,所以才会有“戈多是谁?”“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戈多到底代表着什么?戈多是否存在?所有的未知答案,都将这个故事引向了等待本身,而不是等待的对象。正如《简单的激情》中,A.先生,因为有家庭而不能随意邮件来往,加之战火纷飞,不知道那一通电话什么时候会响起,是哪一天?哪一年?一切都成为未知数,何况这段关系在社会秩序的层面都不具备正面的道德意义,使之更充满不确定性。
无论是等待戈多还是等待A.先生,等待的都是一个无意义的对象。我们一直在打转。但在我看来,等待自身就具有意义。那些不确定的因素——或是不知道何时能收到一条信息,或是明知在现实层面不可能但仍在梦境和幻想中存在的可能性,本就构成了激情和欲望的来源。等待中,我们获取极大的自由,因为它本身就是“某些对幸福的承诺”。
所以说,等待中开展的想象叙事,其独特之处,不在于可以胡乱地天马行空,而在于它游走在现实和梦幻之中,甚至可以模糊二者的界限,同时给我们提供一个自我反思、自我构造和想象的契机,在这之中我们甚至能够获得对自身的确认。所以,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用一生的荒芜都持守在等待之中;《简单的激情》中的“我”清醒地沉沦,乃至于再次用创作这本书的方式,延长等待的周期,确认流动的激情。无目的的等待不要求一个结局,对它的评价,比起说是想象的虚构和主观,我更愿意说它是自由,是意义的重构,我们等待的是一种可能性。这是我的等待,我的重新构造。而等待的答案,需要每一个读者自己为自己编织。
原标题:《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试图叩问“等待”的答案》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袁欢
本文作者:郑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