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年4月,新茶刚上市,有一天,我们进厂后住在同一宿舍的学徒工们忽然议论起了茶。车间有个团干部姓朱,大家叫他“朱头”,他说最好的春茶一斤价格不超过50元。一个绰号叫“格算”的同伴马上反驳:“有超过50元一斤的,你怎么讲?”“你买来!我请客大家喝!”“朱头”很爽气。
这个“格算”在车间做滚铣床,精于计算,因此在我们这批徒工中,技术算是学得很好的。无论车钳铇铣工,做汽车齿轮配件,在检验产品合格时,都允许有几毫米范围内的误差。但凡检验“格算”经手加工的,误差往往是最小的,有时甚至可以精确到无误差。在生活中,他也精于计算,凡划不来的买卖他从不做。周末,郊区工厂的青工纷纷回市中心区,之前都会去工厂围墙外的南大街菜市场,买些农副产品捎带回家。这个“格算”在讨价还价时,常常把菜农杀价杀到几乎无利润可赚。久而久之,我们就给他取了个绰号“格算”。
与“朱头”为春茶价格打赌后的那个周末,“格算”照例乘厂里班车回市区。待到下周一,他果然买了昂贵的“碧螺春”来,下班后他在宿舍里轻轻地打开茶罐,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再看茶叶,全是嫩绿的芽头,外里蒙着薄雾般的细茸。我们几个出身贫寒的“学生仔”从未见过如此好茶,一下子全激动了,“喝!喝!”宿舍里喧闹一片,青春在嚷嚷声中骚动。
“慢!”“格算”贼忒嘻嘻地笑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发票递给“朱头”:“眼睛张张大,看看啥价钿!”“朱头”接过发票,一边看,一边喃喃自语:“哪能价钿介大?”我瞥了一眼,上海黄山茶叶店的发票,上面写着:特级碧螺春,2两,13元。我不由伸伸舌头,真的那么贵,那价格每斤65元,超过了“朱头”最初说的最贵不过50元。“格算”手下留情,只买了2两。但13元钱,按当时的水准,已超过了我一个月一日三餐的全部伙食费,对月收入仅17元8角4分的学徒工来说,确是一笔巨资。
“哪能讲?”“格算”看着“朱头”,目光不依不饶。“朱头”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微颤,但他还是很有勇气地手一挥:“我请客!”于是宿舍里又一阵起哄,鼓掌,喝彩。
有一句说一句,“朱头”的豪爽坦气,是“格算”所远不能比拟的。他的慷慨一直到老,多年后他辞职下海当企业家,每有同事聚餐,都是他做东买单。前些年,我有新著在嘉定新华书店签售,他得知后专程从市区赶来捧场。下午的签售会,他上午就来,中午还招兵买马在饭店叫来昔日同事,祝贺我的新书发布。
那夜,宿舍里一片喧哗、忙乱。有的提竹壳热水瓶去楼下大炉间泡开水,有的乒乒乓乓地拿出玻璃杯、搪瓷杯,连食堂的搪瓷碗都用来充当茶具,很有点“小贼出外快”般的兴奋。我把“朱头”拉到一旁,悄声问:“这么说你要为这一小罐茶叶白做大半个月?”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没有办法的。我说话不作数,你们以后还有谁听我!”“朱头”这时倒坦然了,没忘自己是团干部。“朱头”在车间里做钳工,专门为飞轮齿圈倒角,想着他常常汗流浃背、油污一身,我有点同情他。
第一次喝如此好茶,大家都有点贪,往杯里抓茶叶的时候,量都比平时多。开水冲泡后,那早春茶的清香满屋弥漫,没喝都有点微醉,待一上口,便异口同声说:“味道好!”有的还笑谑地谢着“格算”,说是“格算”让我们领略了一回什么是极品茶。“格算”很得意地瞥着“朱头”,说要谢也该谢他。就这样,大家一杯杯地消受,飘飘欲仙,其间,不时有人小跑着上厕所,从楼上奔往楼下的木梯声都是兴奋的。
折腾至半夜,茶罐已空。我微酣,大脑神经却异常活跃,在床上转侧难眠,翻来覆去的,以致那张上下铺的木床吱吱嘎嘎的发了一夜的奇怪声音。此种状态正是茶醉。有人更是醉态百出,“格算”接连呕吐了几回,最后连胃里的清水都泛出来,我笑他:“这回你也没什么‘格算’!”“朱头”一边骂娘,一边嘀嘀咕咕地抱怨这茶太贵。也有大哭大笑的,其神态绝不输于酒醉的。我记不清是谁,唱了一夜的革命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之类的,到后来还大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时过境迁近一个甲子,回想当年那夜茶醉情景,竟觉梦一般美妙。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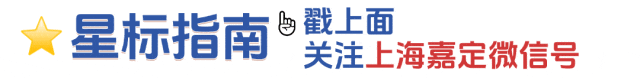





点赞分享给身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