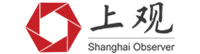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一个人再谨慎,他对我说,年轻时也难免会说过一些话,甚至做过一些事,后来想起来,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恨不得当初没说过那些话,没做过那些事。但他完全没必要去后悔。因为他必须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在达到最终阶段之前,历经种种可笑甚至可憎的阶段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智者。”日前,上海翻译家周克希出现在央视《朗读者》的舞台上,为观众朗读了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中一段关于人生选择的描述。普鲁斯特51年的人生经历中有17年在写《追寻逝去的时光》,周克希则用12年的时间,为中国读者搭起通往普鲁斯特的桥梁。
受到父亲的影响,周克希最初走上了数学之路。周克希早年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但他心里一直装着文学梦。1980年到1982年,巴黎高师的公派学习给周克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到了巴黎好像胆子变大了,突然觉得改行也没什么不可以。”翻译家柳鸣九的研究生金德全邀请周克希翻译一篇波伏娃的中篇小说,周克希在翻译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白天周克希研究几何,闲暇时间,他沉迷在大仲马的文字里,这样的双重生活交叠了10年。他成了数学系副教授,也有了自己早期翻译代表作《基督山伯爵》《不朽者》。半路出家的周克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星期天对他而言,是星期七。不到万不得已,周克希都不会去上洗手间,“我怕脑子里有些东西一下子会没了。”
双重生活下,周克希的失眠越发严重,只能用安眠药助眠。起初,他怕自己得帕金森变笨,翻译家陆谷孙的开导让他卸下心头大石。“他吃了十几年了,我想要是能笨成陆先生那样,也可以了。”50岁时,周克希决定告别数学,成为职业翻译家。“我已经酝酿了十年,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并不难。”这一决定让他的老同事、老朋友都不理解,连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总编都劝周克希好好思考,但周克希心意已决。
翻译的道路布满孤独,尤其是当他开始独立翻译普鲁斯特时。普鲁斯特思想深刻,常会用大量篇幅的长句描写简单事物。整套《追寻逝去的时光》中,有四分之一的句子超过10行,大从句里嵌套小从句,小从句里包裹同位语。当年,周克希在作为15名译者之一参与翻译《追忆似水年华》后,曾笑着和家人说,再也不碰普鲁斯特了。但当别人邀请他再度翻译时,他却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
翻译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时,周克希每天能翻译4000字,但面对普鲁斯特,他每天只能翻译400字,一页纸不到。周克希回忆,那段时间,自己像在隧道里独自行走,看不到前面的微光,但还得慢慢地往前走。12年的时间里,他很少旅游,极少应酬,能用的时间都放到了翻译上,但觉得还不够。
翻译就像化学反应,需要催化剂,而周克希的“催化剂”就是对文学的真爱。虽然没有完成翻译7本的心愿,但第一卷、第二卷、第五卷超过110万字的译作,已经成为中国读者了解普鲁斯特的桥梁。
早年《追寻逝去的时光》被定名为《追忆逝水年华》,是根据英译本书名而来,但周克希觉得,比起好听好记,遵循普鲁斯特的想法,才是重要的。“他不只是在回忆,他是在追寻。”《追寻逝去的时光》中,很多细节都是周克希一一考证后敲定的。小到一个配角的称谓,大到一处环境的描写,周克希都会仔细琢磨。他在《朗读者》录制时对主持人董卿开玩笑说,那几年他联系最多的人,就是法国的普鲁斯特研究者们,自己都快没朋友了。“普鲁斯特面前,一点容不得分心。”
普鲁斯特盛名背后,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周克希的努力。但周克希自己并不在乎。在他心中,理想的译文得像原作者的中文写作才行。他认为,翻译像玻璃,玻璃加工越精细杂质越少,人们越不容易感觉到它的存在。翻译者们也应该让读者感受不到翻译的存在,直接看到作者。
周克希告诉董卿,即使《追寻逝去的时光》读者寥寥,自己也不会挂怀。“读者少又怎样?好的作品,你放五年十年,它还是在那里。”
图片来源:节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