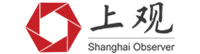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与复旦大学有过多次交集:他的代表作《雷雨》的上海首演,是由复旦剧社担纲的;另一部剧作《日出》的全国首演,其演职人员主要是复旦人;抗战期间,他还到过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任教……
然而,关于曹禺与复旦交集的史料却比较零散甚或稀缺,在一些权威的传记和年谱中记载也不完整。因此,在汗牛充栋的曹禺研究资料中,去发现“曹禺与复旦”的历史细节,是一件令人兴奋而有意思的事情。
《雷雨》排演:请靳以顶替题字
1934年7月,曹禺的剧本《雷雨》在《文学季刊》上全文发表,引起热烈反响。11月起,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学生会、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六一剧社等学校剧团,纷纷排演《雷雨》。1935年4月,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雷雨》,立刻轰动日本。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排练并公演了《雷雨》。10月,由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天津新新戏院演出《雷雨》,曹禺亲临现场,并在后台“亲自为演员提词”,演出圆满成功……戏剧舞台上 “《雷雨》热”持久不散,被茅盾先生誉为“海上惊雷雨”。
恰在此时(1935年9月),复旦剧社创办人、正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洪深先生从青岛返沪。复旦剧社的同学去看望他,称剧社想排演俄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洪深推荐说:“有一个中国的《雷雨》很好,你们可以演。”于是,复旦剧社决定排演《雷雨》。
自当年10月起,《复旦大学校刊》在一个月内先后刊登了《〈雷雨〉的检视》《戏剧与社会现实》《浪费的争论》《并非〈浪费的争论〉》等文章,对《雷雨》展开热议。议论的过程,实际上也为复旦剧社公演《雷雨》做了预热。其时,《校刊》还常在文末刊登《雷雨》演出预告:“请注意:公演日期及地点。”
12月12日,复旦剧社在《申报》上刊登启事:“敬启者:敝社第十九次公演早经选定曹禺先生之《雷雨》,特请欧阳予倩先生导演排练,历四月,兹定于本月十三、十四、十五日假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公演。特此奉闻。敬希光临指导。”其时,复旦已拥有可供戏剧演出的复旦体育馆,为什么还要选在西藏路演出《雷雨》呢?我估计,复旦体育馆虽好,但在当年尚属偏僻。西藏路位于市中心,选址这里,便于一炮打响。13日至15日,《雷雨》在宁波同乡会正式公演,欧阳予倩导演,顾仲彝统筹,胡会忠饰周朴园、凤子饰四凤、程传洁(后为黄蒂)饰鲁侍萍、李丽莲饰繁漪、顾得刚饰周萍、丁伯骝饰周冲……所有演员中,除李丽莲为影剧明星外,绝大部分为复旦剧社学生,这是《雷雨》在上海的首演。
对于这次演出,扮演四凤的凤子体会很深:“谁也知道非职业剧团的难于导演,不过,欧阳先生是认真的,在排练的时候从来不给我们有一点疏忽,如果某一个演员在排练之时懈怠了他自己以致影响到整个空气的话,他会正色地说:‘我不排了!’因此没有一个演员敢于玩忽了他本分内的工作……”(封禾子《〈雷雨〉演出赘语》)正因如此,凤子在演出中非常投入,几次泣不成声。凤子的老师、中文系教授赵景深先生观剧后给她写信称:“馥泉(指复旦教授汪馥泉——引者注)对我说,仲彝告诉他,后台有演员真的哭了一点多钟,大约就是说的你了。”(赵景深《〈雷雨〉的尾声》)
这次上海首演获得巨大成功。演出结束后,有记者采访欧阳予倩,请他谈谈对复旦剧社的印象。他说:“复旦剧社是个纯学生的组合,非职业剧团可比,因此我说这次上演《雷雨》的成绩是不能算十分坏的。他们都很年青(轻),肯学习,肯虚心接受批评,他们的前途,是都很有希望的。”(一芹《〈雷雨〉在上海》,《益世报》1935年12月16日)欧阳予倩的这个说法,很快就成了现实:复旦剧社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了专业演员和导演。
不过,这次演出也有瑕疵,有人就对宁波同乡会的场地不满意:“最引为憾事的,就是剧场太不适宜,否则《雷雨》的演出上一定更有很好的效果。”(张严《观〈雷雨〉后》,《复旦大学校刊》1935年12月16日)这大概就是后来《雷雨》改在新光大戏院演出的原因。1936年1月10日至12日,复旦剧社在新光献演《雷雨》。《申报》刊登海报称:“剧本是曾获得一九三五年至高的评价,导演是中国舞台技巧最精细的专家,演员是久经锻炼的学校剧人,集成功的著作、成功的导演、成功的演员,完成这一时无两的演出。”
应该说,《雷雨》在上海首演,是曹禺与复旦的第一次交集。据凤子回忆,曹禺曾为此次演出题了字。但赵景深的记述略有不同,他说:“曹禺因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便请复旦的老同学靳以(章方叙)来冒名顶替,我被曹禺瞒过,回信给他说:‘你和靳以真是好朋友,连字也像他。’”(赵景深《记曹禺》)
《日出》首演:不满删除第三幕
曹禺与复旦的再次交集,是《日出》的创作与首演。
《雷雨》大获成功后,曹禺于1936年5月起开始创作《日出》。有人说,《日出》中的方达生,是以靳以先生为模特的。靳以是曹禺南开中学的好友,也是复旦商科毕业生。他在复旦读书时,曾与“复旦皇后”陈鼎如恋爱。1932年毕业后,两人分手(陈后来嫁给了一位银行家)。为此,靳以一度痛不欲生。曹禺知道后,特地从天津赶到上海,安慰靳以。“我去找那个女的谈,这个女的不愿意见我,把我拒之门外,对靳以也没有任何表示,真是毫无办法。我只好看着他痛苦,我也跟着痛苦。”(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访谈录》第132页)因此,曹禺在写作《日出》时,自然很有可能将靳以的形象融入他笔下的角色中。
1936年冬,复旦剧社的凤子、吴铁翼等已经毕业,因为原来演出《雷雨》的热情未减,他们自行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上海戏剧工作社”,作为复旦剧社的校友剧社。戏剧工作社首次排演的作品,就是曹禺的新作《日出》。1937年2月2日至5日,戏剧工作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正式首演《日出》——这也是《日出》的全国首演。导演欧阳予倩,凤子饰陈白露、丁伯骝饰方达生、吴铁翼饰张乔治、高步霄饰福升、苏菱饰小东西。
这次《日出》首演实际上是删节版,欧阳予倩导演特地删除了第三幕“妓院”。为什么要删除第三幕呢?欧阳予倩认为全剧太长,而“这幕戏奇峰突起,演起来却不容易与其他的三幕相调和……还有一层,南边人装北边窑子不容易像”(欧阳予倩《〈日出〉的演出》)。而凤子则解释称,“因为女演员本来不多,要排第三幕妓院一场有困难……导演欧阳予倩先生叹说:‘我欣赏第三幕,剧社没有女演员,导演怎么办?’”(凤子《重访“一桥讲堂”》)
然而,删除第三幕,却让曹禺颇为不满。曹禺曾由靳以陪同,特地到上海卡尔登大戏院观看了《日出》首演,他晚年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那时,我年轻气盛,是不满意欧阳予倩导演的《日出》……他们的《日出》,我看了,凤子的演出是很好的,但是对于没有第三幕,我是不满意的。我说,这是把这部戏的心脏挖去了。老先生(指欧阳予倩——引者注)一定不满意我,我是当面说了这句话。”(《曹禺访谈录》第158、159页)据说,欧阳予倩知道曹禺的不满后,叹道:“虽然不能承受这罪名,但是对作者真是有说不出的歉意,怎样让作者明白我的用心呢?”(凤子《台上·台下》)
不过,到了晚年,曹禺还是坦言,虽然对拿掉第三幕有意见,“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对这次演出全盘否定。相反,我对他们的勇气,对他们的演出是充满感谢之情的……意见归意见,感激归感激。我不会忘记这些戏剧界的朋友们”。(《曹禺访谈录》)
到复旦任教:叫座又叫好
1942年夏,正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任教的曹禺,忽然辞去教职,到了重庆。据田本相、阿鹰编著的《曹禺年谱长编》记载:是年10月,曹禺“受聘复旦大学外文系”。不过,查阅复旦大学档案馆的聘书存根,我却发现,曹禺(聘书上写的是曹禺原名万家宝)受聘于复旦,要早于1942年。

曹禺1938年3月受聘复旦中文系兼任教授聘根(复旦大学档案馆藏)
早在1938年3月,曹禺就已被复旦中文系聘为“兼任教授”,“每周授课叁小时,每小时薪金肆元”,聘书签发者为代理校长钱永铭(钱新之)、副校长吴南轩。上述聘书存根,就可以解释叶圣陶在当年3月27日写信中提到的曹禺:“此君能干,诚恳,是一位好青年”“这个星期四,将往北碚复旦上课,曹禺也有课,约定同去……预定在那里上课之后,玩各处风景,在温泉洗浴,松散一天,到星期六回来”。(叶圣陶《渝沪通信》)曹禺则记得:“1940年,我和叶老都在复旦大学教书。学校在北碚,我们住在外边,经常两个人碰到一起,在码头上等船,坐船去学校,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在一起闲谈。他确实有一种宽厚长者的风度,是非常容易接近的。”(《曹禺访谈录》)
到了1942年8月,吴南轩校长又向曹禺签发了新聘书:这一次,曹禺由“中文系兼任教授”转为“外文系专任教授”,聘期一年(1942年8月至1943年7月),“每周授课九小时,每月薪金国币四百元”。一年以后(1943年8月),章益校长也续签了聘曹禺为“外文系专任教授”的聘书。因此,自1942年8月起,曹禺正式成为复旦“专任教授”。但我以为,曹禺在复旦的任教日期,应该从1938年3月算起。

曹禺1942年受聘复旦外文系专任教授聘根(复旦大学档案馆藏)
曹禺到复旦任专任教授,令其他学校学生羡慕不已。据说在几年前,就传出曹禺有意在上海暨南大学任课的消息,暨大甚至已排出了他授课的课程表,学生们为此奔走相告,“以为可以一瞻这位名震遐迩的戏剧家的丰采,可以亲近地听到他滔滔的宏论,有些学生是着了《雷雨》《日出》的迷,还声言着,要曹先生详细述说他的创作经过,或是‘表演’一番呢”。结果,曹禺并未成行,暨大学生深感失望,“而,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学生,却幸运地得到了他……学生们都兴奋百倍”。(《曹禺执教复旦》,1943年4月4日《东方日报》)
在复旦,曹禺主要教授“戏剧选读”“英国文学史”“英文”三门课程,他的课深受欢迎。每次上课,教室内外挤满了人,“听的人多,要早占座位,去晚了要坐在地上,曹禺来时,要高抬脚,跨过一个又一个席地而坐的听课学生,才能登上讲台”。(邵嘉陵《夏坝学人芬芳圃》)据1943年10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所刊的“复旦琐记”称:“本期叫座最多的教授,计有方令孺先生的国文,万家宝先生的英文……以及洪深先生的文学批评等课。”
关于曹禺的上课细节,当年的新闻系学生邵嘉陵先生在《夏坝学人芬芳圃》中有过一段精彩叙述:
如果说,洪深上课是黄钟大吕,曹禺的课却是玲珑剔透了,他不像一般的老教师那样:上了讲台,摆好课本,摊开资料,拿起粉笔,然后滔滔不绝地讲开。曹禺却是慢条斯理地,拿起讲义独白:“走向地狱的道路要早点铺成”,说戏剧的序幕要铺排得快。这是独白,因为他边讲边思忖,边进入角色。这是说,他“目中无人”。他看见了地狱,并且痛苦地向前走,还要快走。他的演出开始了!
曹禺讲课是标准的普通话,口齿清楚,娓娓动听,就好像是看演出一样,讲什么人物,他就是什么人物。有时,他把对方提出的问题,说:“一个浪冲来”,极有诗意。
上曹禺老师的课,有轻松、细腻、透彻、愉快感,非常温暖,不觉得吃力,只觉得时间过得快,不想下课,也不觉得人多。一旦下了课,却真有些累了。
曹禺是何时离任复旦的呢?有关传记和年谱均未有答案。复旦档案馆收藏的一则“校长室致总务处、会计室、出纳组的通知”称:“文学院外国语文系专任教授万家宝薪津、食米停发等因相应通知,即希查照。”落款为“卅三、四、八”,也就是说,1944年4月,复旦停发了曹禺薪资,可见其时他已不在复旦任教了。
曹禺先生晚年,与复旦仍有交集。1984年5月,原复旦话剧团演员、复旦中文系教师廖光霞访问日本,在关西大学观看了日本学生演出的《雷雨》。回沪后,她就将此次演出说明书寄给了曹禺,曹禺回函表示感谢;1986年4月22日下午,复旦外文系师生用英语演出《无事生非》,正在上海参加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曹禺,兴致勃勃地前往观看。当他在谢希德校长陪同下步入相辉堂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谁也不清楚,此情此景,是否勾起了曹禺对复旦往昔的温情回忆……